「我有決心(will)成為現在的我,我將(will)成為的也只是現在的我。」
這句神祕的話語,連同那把樸素的銀鑰匙,就放在黛安娜遺囑所附帶的信函裡,交給了家中的次子。雖然家族規定這件遺物只能母傳女,可是由於她只生了兒子,所以讓她在臨終時還為了這些代代相傳,看似古怪且毫無意義的傳統而傷透腦筋。原本,在沒有女兒的情況下,這件傳家古物應該傳給長子亞歷斯,然而臨終陪她的卻是次子威爾,加上她對兩個兒子一視同仁,讓她不禁覺得威爾才是適當的繼承人。她相信這樣並不算違背規定。
亞歷斯結婚時,她就一直等著抱孫女:只要生了孫女,繼承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但由於醫生的工作壓力太大,必須隨時待命,使得亞歷斯在家的時間少之又少,他的婚姻遺憾地劃下了休止符,讓她無法如願抱到孫女。而威爾呢,她很清楚最好別期待他會結婚。威爾才華洋溢,愛心滿滿,待人親切,雖然暴躁易怒,卻是性情中人。女人往往不由自主受到威爾吸引,迷戀他英挺的長相和結實的體魄。其實她的兩個兒子都是出色的運動員,兩個兒子都在村子裡打板球,而且如果威爾願意,或許還有資格參加國家代表隊。威爾曾以拙劣但有效的姿勢,奪得「最佳板球手」的稱號,而且還利用反方向助跑的欺敵戰術,趁所有觀眾捧腹嘲笑的同時,意外傳球得分!當時有好幾位球探想簽下他,但威爾拒絕。他只想為玩樂而打球,不想將它變成賺錢工具,他更不願意為了練球而放棄假期——這就是威爾。
她原本以為威爾的前女友仙恩會逼婚成功,因為熱情、迷人的仙恩已經三十歲了,很希望可以早點成家。若真的結婚了,威爾說不定就會生個女兒。儘管威爾的外表看來粗獷陽剛,內心卻十分細膩,或許生了女兒以後,他就會成熟,有父親的樣子。她把一切交給時間和仙恩的執著,再把銀鑰匙留給威爾。黛安娜將銀鑰匙、一張古老的羊皮紙,以及她寫的字條放進大信封袋裡,字條上寫著:
「給威爾,當他不再是他現今樣貌,或者不再是現今這人時。」
對此,她未多加解釋,即使在臨終與他道別之時。
威爾將這奇特的護身符當作珠寶般端詳,在燈光底下瞧了又瞧。他曾在其他狀況下檢視過這把銀鑰匙:深夜的碼頭;彷彿有惡魔虎視眈眈的黑暗房內;母親葬禮過後的一月寒風中;義大利的神廟谷裡;以及梵蒂岡閱覽室的小小空間中,他耗費了許多時間,搜尋著百花廣場的晦暗傳說。這把銀鑰匙似乎帶有某種象徵,卻不知究竟鎖住了什麼?可以被它開啟的鎖彷彿已隨時光消逝,埋藏於歲月的漩渦之中。他甚至找不出這把鑰匙是從何時開始流傳的。威爾對母親家族的歷史了解有限;而父親也反常地不願多置一辭。
我即是我,及目所見。
他在前往夏特爾的最後一段路途中,仍死命想著這句話。他已經將羊皮紙上的字句背得滾瓜爛熟了,此刻,他一面思索古羊皮紙上的文字,一面仍高超地駕馭機車。威爾甚至還把這句話影印下來,收在皮夾克內裡的口袋中,隨身攜帶。即使當他夏季前往酷熱的西西里時,他仍穿著皮夾克,不願和這珍貴的遺產分離片刻,至於那把銀鑰匙,他則穿了鍊子戴在脖子上,除非他掛了,否則永不分離。他知道哥哥亞歷斯對於這件事絕對有不同的解釋。亞歷斯的思緒,總離不開他的工作、研究報告,以及他和兒子麥斯的關係等等。但威爾不同,他凡事一定追根究柢,全神貫注,直到謎題解開,或許直到找出與銀鑰匙對應的鎖,才會罷休。威爾懷疑自己的身分也是謎團的一部分,而銀鑰匙背後代表的「珍貴寶藏」並不是促使他解開謎團的動機。他對於黃金珠寶根本不感興趣,威爾想知道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事情這麼重要,值得代代相傳至今。
威爾是個人脈廣的自由攝影記者。某次跟一位老同事喝啤酒聊天時,那位同事被威爾所說的謎吸引住了,主動提議要幫忙把羊皮紙送去一位在牛津工作的表哥那兒,做碳十四年代鑑定。這樣他們起碼會知道紙張的大概年分。等結果出爐之後,那位同事傳簡訊給威爾,當時他恰好坐在義大利西西里的塔奧敏納希臘劇場裡:
樣本測試了兩次,兩次都落在十六世紀末。想知道原因嗎?九月見。——賽門
想,當然想!十六世紀末的百花廣場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儘管他是填字遊戲和變位字謎的高手,但也猜測不出這列字串和銀鑰匙究竟有何關聯,而這還只是謎題的一個開端而已。
經過好幾星期的奔波與研究後,威爾開始有點眉目了,但他仍被各種不確定的事證搞得七暈八素。他趁著在羅馬的最後一天時,將十六世紀羅馬政治背景資料以電子郵件傳給自己,並且在網路書店上訂購了成堆的書籍寄回家。他對於倩契這位在十六世紀末成為羅馬一樁兇殺案主嫌的義大利貴族女子,還有被燒死的布魯諾,以及伽利略都大感好奇。而且他越探究這些資料,就越覺得自己身處在詭異的巷弄,身旁不時經過一排排跳著宮廷舞、戴著兜帽的陰鬱身影,他猜想這或許就是所謂的「丑舞」,偶爾這些巷道會轉為死胡同,只留給他一種詭異的不安。
羅馬可能會令你忍不住頻頻回首,即使你的身後除了一堆偏執狂以外,其餘什麼都沒有。
儘管機車的安全帽讓視野變窄,威爾仍可以看見飄浮於數英哩外平原上方,夏特爾大教堂的壯觀身影。他飆速前進,看見教堂巨大的形影突然聳立眼前,不難想見中世紀的朝聖者在面對如此龐然巨物時,會感到自身何等渺小。他明白這座聳立於地平線上的偉大教堂身影,永遠都會深深吸引著他。
威爾繞過一個彎,將車速減慢,機車立即變得沉重,他必須專心才能讓自己順利通過從中世紀留下來的迷宮般小路。之前他曾因為不熟悉操作,造成兩次失速。如果不好好對待這輛機車,它保證讓你吃不完兜著走。他騎車進入禁行區,也不管路旁的停車標誌,就直接朝尖塔騎去。當他穿越畢勒廣場,順著向善路騎騁,機車引擎的呼嘯聲劃破了小鎮修道院般的寧靜。他繞過大教堂南側。這時正接近中午,教堂對面一家小餐館傳來法式洋蔥湯的濃郁香味,提醒他久未進食。等他拜訪完此地後就該去吃點東西了。
他騎車趨近教堂,抬頭望著那兩座熟悉的高低尖塔,並在壯麗的西門陰影下停車,脫掉了安全帽,以示騎士的禮節。正當他的眼睛適應了子宮似的黑暗,耳朵便開始聽見來自不同角落、各國旅遊團的導覽低喃;所有的遊客都對他頭頂上方的彩繪玻璃發出無比讚嘆。原本威爾也是打算來觀看這個的,但他的目光卻立刻被另一個景象吸引。他雖然來過夏特爾大教堂不下數十次,卻不記得自己曾見過教堂中間的地板。
當座椅被移撤後,地板上清晰地露出了鑲嵌於哥德式中殿地面的巨大黑白圈紋大理石。彩色玻璃的燦爛色彩灑滿了整座教堂地面,壯麗得令威爾目不暇給。在地面的正中央,有名女孩正閉眼佇立,但不妨礙他看清楚地面的花紋圖案。這教堂他來過好幾回了,卻未曾注意地板。
附近有個法國少女正對著一個旅遊團作解說,她的英語不錯,聲音也算甜美。他心想,又是一個暑假打工學生。
「這是著名的夏特爾迷宮,各位也知道,迷宮的傳統流傳已久。許多國家都有迷宮,可是當你在一座如夏特爾般的中世紀大教堂裡見到迷宮,這項異教的象徵顯然蘊含著強烈的基督教意涵。我們知道歐瑟爾大教堂、亞米恩大教堂、里姆大教堂、桑恩大教堂,以及亞拉斯大教堂裡都有迷宮。但由於十七和十八世紀的人不了解迷宮,所以這些迷宮都被拆除了,只剩下夏特爾迷宮保存得最完整。我們知道,神職人員常常會被那些來走迷宮的民眾騷擾……」
威爾覺得法國女孩講得不錯,於是走近些去聽。她注意到他不是團員之一,對他笑了一笑。或許是威爾將欣賞之意傳達給她,讓她有點信心繼續說下去。
「……夏特爾迷宮建成於一二○○年。請各位再看一次位於它後方西側,那扇最後審判的玫瑰花窗,這花窗製作於一二一五年左右。各位會發現迷宮的距離與尺寸幾乎等於地面到門、門到玫瑰窗。這強調了一件事,那就是跟著地上的迷宮路徑就等於跨上樓梯的一階,通往上方的世界。迷宮在柱子之間最寬的距離是十六點四公尺寬,各位請記得,這是法國最寬的哥德式中殿。如果我們像中世紀的朝聖者那樣走完全程,那麼總長就會超過二百六十公尺。這段路程向來被比喻為『通往耶路撒冷的旅途』,我們了解朝聖者可能跪著走,作為贖罪的一種方式。因為在那段時期的地圖上,耶路撒冷被畫成世界中心;即使到了現在,對於許多信徒來說,最後的審判仍與耶路撒冷和大神殿的預言息息相關。現在請各位跟我來,我們接著要看的是亞當與夏娃窗。」
當她把手掌往上翻,要大家跟著走時,威爾輕碰她的胳臂,以法文說道:「小姐,不好意思,打岔一下;我以前沒見過像這樣的迷宮花紋——直到今天才親眼目睹……這太令人驚嘆了!」
對於威爾的打岔,法國女孩並不以為忤,她也以法文回答:「你今天不就看到了嗎?每個星期五都有這樣的導覽!從四月到十月的每個星期五。」她親切地笑起來,然後安靜地帶著她的團員離開。
一名女孩剛走完迷宮的路線,此刻從中央走出來。她的眼睛睜得很大,臉色有一抹緋紅。
「對不起,她剛說只有星期五開放,對嗎?那麼我趁著秋分的今天前來,還真是來對了,而且過了今天以後,陰性的力量又會主宰到春天。」她是美國人,面容清新,舉止大方,對著威爾笑了一笑。「你也應該去走一遍。會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而且現在的光線恰到好處,很適合走看看。我剛剛等了很久,等到沒人了才有辦法走。你應該也來試試。」
威爾對她點頭。「好,謝謝妳。」
但他卻有點遲疑,因為他不算是個對信仰虔誠的人——至少不是以傳統的角度來看。威爾在某層面上相信信仰,認為的確有許多事情是超乎人類理解之外,但基本上,他並不相信處女生子這件事,更不會輕易跟別人分享自己的心靈。但他發現,他的雙腳居然不自覺地開始往迷宮起點的方向移動。
「好吧,好吧。」他心想:「就當作是星期五的特別活動吧……」他自顧自地笑笑。「加上今天又是秋分。」他反諷地說完最後一句。威爾不認為這位少女非常特別——他沒有批判的意思——但一位如此可愛的少女,居然會對秋分重視到這種程度。
威爾開始走入唯一的迷宮入口。他朝祭壇走了三步,然後順著迷宮的路徑左轉,進入一個美麗的弧形路線,弧形接著隨即繞回路線本身。起初因為路徑窄小,他得盯著自己的腳步,小心翼翼地遵循迷宮走向。他注意到他所走的是淺色路徑,並且以較深的輪廓線勾勒出來,象徵著足踩光明,避開黑暗。
他把安全帽抱得更緊,閉上眼睛一會兒後,不再全神貫注盯著腳步,反而改以輕鬆的步伐前進。第二圈幾乎將他帶到中央;他原本以為迷宮會突然抵達花形中央,但經過一小段奇幻的曲折路徑後,又轉回了原地,整條路線像一條美麗的蛇,直到再度出現一個大型的弧彎,帶領他接近中央,然後又繞出去,進入另一個四分之一圓弧。
威爾的眼睛受濃郁色彩的吸引,南面窗所投射出的色彩,在他臉上形成斑駁的光影,讓他沉浸其中。他停頓一下,仔細觀看眼前的圖案:一個男人從城牆的大門出現,背景是鈷藍色的玻璃;在圓形窗中,有個人在他背後鬼鬼祟祟,而且正要從鞘裡拔出劍,背景是絕妙的紅寶石色。拔劍的人身穿綠色,被畫得很好,而他前面的那個男人則身穿藍袍,肩上披著黃色披風。紅藍黃三原色隨著秋分近午的陽光穿透玻璃,落在威爾臉上。威爾感到輕飄飄的;這次的體驗出乎他意料地深刻動人。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提醒自己別入戲太深。
迷宮上空無一人,好像大家都慷慨地把空間留給威爾,儘管他意識到身旁有人正訝異地觀察他,但威爾毫不在意,反而還十分享受自己的臉從明亮轉入黑暗,再從黑暗回到光明的感覺;他的雙腳在曲折的迷宮中來回遊走,彷彿是一場複雜的捉迷藏。母親在遺囑中寫下的字句像咒語般,在他的腦子裡響起……

在百花廣場燃燒的一切!摘下一朵花,思索曾經歷過的事;
思索幾百年來的
背叛,與痛苦,與誤解……
威爾閉著眼睛在迷宮繼續漫遊,不自覺地摸著他的夾克,腦海裡只浮現這幾行文字,而且腳步規律地踩向迷宮出口……
我就是現在的我,不是過去或以前的。下定決心成為自己,而不是某某人第二。就算故步自封,如果我決心成為什麼人,我也不想成為別人。如果我曾經是我被迫成為的人,他們也猜不準現在的我或過去的我是什麼。我要打破圍籬,成就自我。
我就是自己的難關,真相便是如此。
而這就是縫隙,右邊和左邊,
憂心忡忡的戀人將透過縫隙輕聲細語。
每一對等於相接的每一片;左下角是個方形;右下角是個方形;左上角是個方形;右上角是個方形。中心也是個方形。

我已經過了軌道一半。如果你取全數的一半,湊成與我相等的對數,你很快就會用光所有的對。
現在,不要看超過這一天。我的α和我的ω,把這兩半形成一個完整的圓。從舊王之書取同號碼之歌。從起點往前走同數目的步子。從終點倒退同數目的步子——只刪除出口的一個字。阿門。
我是現在的我,你將看到的是現在的我。
注意細數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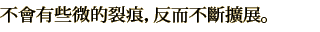
威爾起初感到頭很重,現在卻覺得愈來愈輕。他渾然不知自己引起不少人側目——有個小男孩握住了媽媽的手,有位老太太拿掉眼鏡,毫不保留地注視他的腳步,還有一個活潑的紅髮女子停止與女友的閒聊,不由自主地盯著這俊俏的男子直瞧。有位教士看著他,默認地點頭,在北側圓柱後方的一個男人,似乎被威爾的整個經歷所催眠。他以數位相機拍下了迷宮中的男人。
威爾的雙腳輕輕舞動起來,他口中唸唸有詞,就像在唸玫瑰經般:「我有決心成為現在的我……如果我曾經是我被迫成為的人……」
他已抵達迷宮的中央,臉朝著正西,大玫瑰窗位於他的正上方。八位天使從內層玫瑰中較大的花瓣往下看著他,成雙成對地坐在一隻老鷹、一個長翅膀的男人、一頭牛和一隻獅子之間。他感到亢奮不已,他知道自己並未突然經歷宗教上的轉化,不過他對走迷宮、光線、大教堂裡的各種聲音,以及他自己的心理狀態所造成的效果嘖嘖稱奇。這一切令人迷醉。更神奇的是,他領悟了貼在他心口上那張羊皮紙的某些涵義,這是他原先所不明瞭的。「他」是威爾(Will,決心);他註定要找出鑰匙的依歸,解開它的涵義,發現它的寶藏。也許他不需要如此急迫地追查,謎團最後也會水落石出。
他從中央跨出六大步,有塊鐵修斯7與被他消滅的牛頭人身怪的圖匾曾以鉚釘釘在那兒,鉚釘的痕跡依稀可見。他轉向左邊,聞到清新的玫瑰花香——宛如異國的玫瑰精油香。他的腳繼續往前跨出,當他來到一百八十度轉彎時,以為會看到香味的來源;但什麼也沒有,不見任何人影。他轉向東邊,伴隨著流暢移動行進入線,香味又來了,但那只是光線和他自己的神經質所造成的錯覺,於是他在無人干擾的情況下,走完他的迷宮。
他氣喘吁吁地從位於中殿的迷宮核心,逕直走到祭壇的後方,進入聖母禮拜堂;他在此點燃一大根蠟燭——奉獻兩塊半歐元是值得的。他感到母親與他同在此地,照看著他,於是他無聲地說:「現在的我不是當時的我了。」
他從大教堂的北門走出去,雙腳完全感覺不到與地板的接觸,也渾然未覺有一條黑影在昏暗的燈光中,從柱子後方溜走。
──摘自《玫瑰迷宮》 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