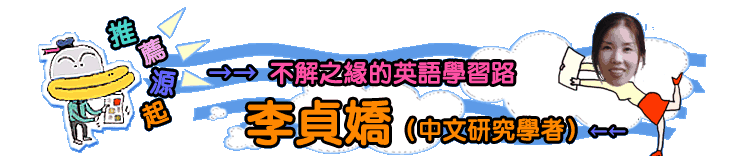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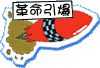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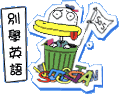

| 我雖然是一名中文研究學者,但從就讀於中文系的大學時代起,就和英語結下了不解之緣,這與我個人坎坷不平的人生經歷是緊密相關的。 我從小就對漢字有著較為濃厚的興趣,隱隱約約地覺得學習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的中文會別有一番意趣,於是便選擇了中文系。但世界並非我想像的那般如意。上大學時,雖然可以用獎學金來繳納學費,但學費以外的其他開銷就得靠外出打工來籌集了。當時我為了準備研究生入學考試而不得不刻苦地學習英文,並以此為契機,當上了補習班的老師。白天學中文、晚上教英語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此後,一直到我修完博士課程的十年間,我一直倚靠教授英語來維持生活。這樣一來,我就同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大語言--中文和英文--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在補習班裏主要教授語法、精讀以及詞根分析,學生們在學校的英語考試中取得了好成績,我也就自然成了頗受歡迎的老師。但當我看到學生的會話能力並沒有提高,甚至連面對外國人都不敢的時候,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之中。但是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六日,我在釜山國際電影節上看到了一部介紹一位年輕有為的中國英語教師的紀錄片,激動得在接下來的近一週的時間裏興奮異常。 這位年輕的中國教師叫李陽。我這樣感動,並非因為他與眾不同的學習方法,而是他那體現於英語學習中、挑戰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雄心和勇氣,給我強烈的震撼和衝擊。從那以後,我每到一個地方授課,都要講李陽的理想,介紹他的「三最法」(最清晰、最大聲、最快速),並打算以我的學生為對象,在中、英文教學中試驗這一方法。而且還下決心到中國去的時候,一定要見他,親耳聽他的講演。 《千萬別學英語》在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一版一問世即獲世人矚目。但我直到那時卻還沒看到過《千萬別學英語》這本書。韓國做為全民對英語學習極度熱心的國家,書店裏擺著那麼多的書,而站在讀者的立場卻難以抉擇到底該選哪一本好,這實在是一大悲哀。為吸引讀者的目光,僅僅用各種浮華的廣告或標新立異的書名,已不能引起更多讀者的注目。一天,我因提前赴約,尚有半小時左右的時間,就順便進書店逛了逛,偶然看到《千萬別學英語》這個書名,禁不住笑了。以為又不知是誰為追求商業轟動效應,起了這麼個稀奇古怪的名字,就隨便翻了翻書的內容。首先,做為英語書卻沒有英語例文,而僅僅有學習方法的介紹,這使我大吃一驚,同時也給了我某種不同尋常的感覺。於是半信半疑地買了這本書,和朋友匆匆忙忙地分了手。回到家裏,我一口氣把全書看完之後,又仔仔細細地讀了一遍,同時針對書中介紹的訣竅做了筆記。 對於有十年外語教學經驗的我來說,既然是好的方法,僅僅自己獨自體會一下就過去了的話,實在是太可惜了。所以從那天起,我就成了《千萬別學英語》的「宣傳大使」。以我的經驗來看,作者提倡使用這一方法的見解絕非欺人之談,意識到這一點,我很是高興。那時的我對作者幾乎是一無所知,不過在電視上播放介紹英語學習方法的節目時略掃過兩眼而已。我意識到這個方法不僅適用於英語學習也適用於所有外語學習,因此決心以此方法為基礎,開發我專門從事的漢語學習方法。於是,二○○○年八月赴北京之際,不顧行李的沉重,我仍帶了《千萬別學英語》和它的姐妹篇《還在學英語嗎?》。 中國人同韓國人一樣,接受的也是以單字、語法、閱讀理解為主的傳統英語教育;理解力固然可以達到相當程度,聽、說能力卻普遍很差。瞭解到這一點,我便向「瘋狂英語」的聽課者介紹了《千萬別學英語》的方法,以聽聽他們的反應,結果,得到了大家的廣泛認可。後來,我進入北大的課堂,發現許多學生,較之集中注意力上課聽講,更熱中於英語學習,於是我以周圍的學生為中心,給他們讀了《千萬別學英語》學習方法的譯本摘要,結果反應非常好,我也因此獲得了勇氣與信心。於是急急忙忙地把譯本摘要貼到北大各個複印室,靜觀其反應。最後又給北大外國語學院的王丹教授讀了這本書,並徵求她的意見,問這本書是否可以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王丹教授欣然回答說,與她自己學習英語的方法相比較來看,這本書的方法的確很好,應該是可以充分引發中國讀者的興趣的。 我對作者所知甚少,僅僅因為《千萬別學英語》是較好的英語學習方法,所以才想把它介紹給中國人;但讀了作者這本新書後,作者正確的價值觀和對生活真誠的態度使我肅然起敬,從而覺得翻譯《千萬別學英語》不能僅僅單純地介紹英語學習方法,對作者獨到的思想和見解也應該努力予以體現。這種判斷大大減輕了我工作的勞苦。最令人高興的是,在這本書的中文版出版以前,它已經得到了中國人的廣泛關注。 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於北大勺園 ───(摘自《千萬別學英語》譯者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