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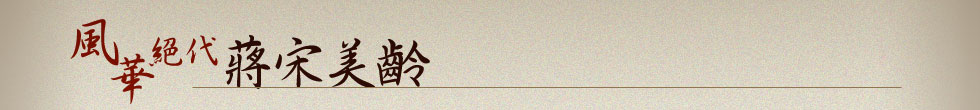
宋美齡新傳 作者:漢娜.帕庫拉 看一個家族如何左右二十世紀中國的發展 最權威的宋美齡傳記;最好看的民國簡史 宋美齡是傳記作家極大的挑戰,她一生經歷重大歷史事件無數,加上性格複雜,形象多變,以致評價兩極。傳記作家遠觀下筆,則面目模糊矛盾,近寫則容易受其魅惑,難以客觀。 帕庫拉以寫作傳記著稱,又是宋美齡衛斯理安的學妹,以大量近年解密的書信文件,把宋美齡、乃至宋氏家族放在民國史的脈絡中書寫,試圖呈現這一位兼受中西文化薰陶的傑出女性,在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nation building)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宋美齡堪稱二十世紀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之一。
宋美齡長於優渥環境,1907年赴美唸書,十年後從衛斯理安畢業,返回繁華上海,成為出入上流社會的名媛。1927年,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登上權力舞台,馳騁過人的才智與精力,舉凡新生活運動、北伐剿共、西安事變,都有宋美齡的身影。 宋美齡左右了二戰期間美國面對中國戰區的動向,把夫婿蔣介石推上國際政治的舞台,甚至也影響了二戰之後美國社會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隨著蔣經國逐漸掌權,宋美齡也淡出權力核心,晚年定居美國,於2003年過世,享年105歲。 【作/譯者簡介】 漢娜.帕庫拉(Hannah Pakula)
林添貴
|
![]()
季辛吉:「蓋棺論定的宋美齡傳記。」 ★名家一致推薦:
★2010.03.14中央社「每週讀好書」推薦:
★音樂劇《世紀回眸─宋美齡》編劇楊忠衡:
★媒體報導:
|
![]()
美齡一回到上海,就接手打理家裡的大小事務,包括管理七男五女十二名傭人。她告訴艾瑪:「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她形容她家是「上海最漂亮的房子之一」,四層樓高、十六間大房,加上廚房、浴室、迴廊和可打盹的小走廊。它位於霞飛路(上海最長的街道),離市中心很遠,使得它很時髦、但不方便,和購物區、戲院和餐廳都有段距離。她說,他們家的傭人房都比她在大學的學生宿舍好。 除了總管家務之外,美齡也負責管兩個弟弟,他們倆在去年才在學校被當掉。她寫說:家人「氣壞了。這兩個可憐的孩子有兩名家教(一個英國人、一個中國人)每天來家裡……兩個男生功課沒過,更加強我的Demarest Scholarship(衛斯理安的學科獎)在家人心目中的價值。他們認為我是個奇才……,我可以完全掌管他們,因為媽媽氣壞了,把他們交給我管教。他們很難管,因為他們非常聰明,可又很懶惰。我好幾次用鞭子教訓小弟弟!而他們都很怕我。妳不曉得我多會教訓人喔!」 美齡在美國就喜吃奶昔和冰淇淋蘇打,回到上海時她的體重在五十七至五十九公斤之間。她媽媽立刻要她節食,直到體重掉到四十五公斤以下;後來一直到老,她都保持苗條的身材。 更難調適的是學習如何融入家庭和國家。她寫給艾瑪:「妳的兩封信剛剛送到!它們就像在沙漠中迷路的異鄉人碰見綠洲!你可別以為我不高興或不滿意我的家庭生活。絕不是的。只是……我還找不到我究竟在哪裡。你建議我在我國人的生活中放輕鬆,正是來得是時候的好主意。你也曉得妳的兩封信剛剛送到!它們就像在沙漠中迷路的異鄉人碰見綠洲!你可別以為我不高興或不滿意我的家庭生活。絕不是的。只是……我還找不到我究竟在哪裡。你建議我在我國人的生活中放輕鬆,正是來得是時候的好主意。你也曉得我是個非常獨立的人,過去十年都只依自己的意志過活。因此,很難去記得我必須想到別人。我也擔心我不是那麼有耐心。」 美齡很想找一份能使自己「忙碌、又覺得有興趣」的工作,她向艾瑪抱怨,她既不能對家庭福祉有所貢獻,又辜負了自己的聰明才智。沒有人作伴,她也到處去不得。「怪的是我竟然一點都不生氣。我只是默默地消極接受。你沒辦法想像我這麼易動怒的人會是如此吧?……我只覺得我的精神力量愈來愈麻木。」 十月十日,美齡和兄弟要求媽媽准許傭人放假,全家人去上海最大的市場走走。她寫信告訴艾瑪:「我們真的在哪裡向攤販買菜耶。我們甚至說服爸爸和媽媽跟我們一道上市場。我們全都穿上最舊的衣服。你可以想像我那貴氣的媽媽是怎麼看待這件事。」上海市場是個「像大帳篷式的結構體,佔地約二公頃」,它有水泥地板、薰黑的磚瓦屋頂,農民租攤擺賣東西。買菜回家後,全家人湊到廚房裡作菜。美齡做的是軟糖(fudge),因為她只會做這一道點心。午餐後,孩子們想去看賽馬,但是「因為爸爸、媽媽被大家視為『教會砥柱』,他們只好改去兜風。「我們回到家,傭人已準備好晚餐,大家津津有味地吃起來。晚餐過後,我們發現幾個不知分寸的傭人沒有請准又溜出去看戲。爸爸大怒,因此下令把門都鎖上。因此這些可憐的傭人必須在馬廄裡凍一夜!我猜他們以後一定不敢開溜了!」 美齡就和全世界備受驕寵的年輕女性一樣,大學畢業後投入社交生活和慈善工作。但她也似乎追求不受限於傳統的活動。美齡不同於一般的富貴階級,愛以她的美國點子和方式驚駭上海社會。她第一份工作是在主日學校教課,是唯一一位女老師、教的是男生班,而學生又喊她「先生」,但是以她的地位而言,並非罕見。她的下一份工作更有趣。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寫信給一位朋友:「我在家裡遊手好閒、無所事事……我可以免費看電影。你猜怎麼一回事?很簡單,因為我是中國電影檢查委員會委員。」她向艾瑪坦白談到她擔任這個職位的資格:「想像一個年輕、純潔、一點也不世故的人……檢查起大眾應不應該看什麼。哈!」美齡也在基督教女青年會做義工,推動組織中國婦女。但是她顯然不以此為滿足。她在回家四個月後寫信給艾瑪:「我認為,我希望做些實質的事情、可以當做事業的事情。我今天這樣的生活,只會走上結婚之路……。即使在大學,除非必要,我絕不勞動。現在我在這方面也沒變。如果我有份職業,我可以迫使自己工作、認真工作……,即使現在我可以感覺到,兩位已婚的姊姊正在傷腦筋要替我促成婚姻大事……。我反對就這樣子被嫁出去。但是我猜想她們的邏輯無可反駁。她們說:『現在你該做出本季最轟動的結合。』……我每天早、午、晚都被疲勞轟炸該成親了。」 她也開始注意到中國的政治,向朋友提到:「到處……都很悽慘!有時候我看到貧民窟那些骯髒、襤褸、擠成一團的人,心裡就想那有可能盼望到偉大的新中國,立時覺得自己很渺小。達達,你沒辦法想像在那樣的環境裡會覺得自己是多麼沒用;此地窮人的百分比遠遠超過你在美國所能想像。」在《京報》(編按:陳友仁所創辦的英文報紙,因發表批評段祺瑞的文章而遭查封)被取締、內閣垮台後,她寫說:「中國政治無可救藥,你根本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你也根本不知道下一次誰的腦袋會被砍掉。」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譯按:美、英、日等國在上海租界合組的聯合管理當局,法租界則自行管理)邀她加入童工問題委員會,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中國人出任過委員。對於曾在美國社會高尚階層住了十年之久的女孩而言,調查上海工廠的工作環境之經驗的確非常震撼。一次大戰後的經濟榮景下,根據一位觀察家的說法這些工廠的環境「有如地獄」。承包商跑到鄉下旱、澇災區,以「極低廉的價錢」買下全村女子,塞進簡陋住家改成的工廠廠房,每天工作十四小時、每週工作七天。一年只在大年初一休一天。 美齡在多年之後說:「我花了很多時間參觀上海各式各樣工廠,對於所謂上海公共租界(主要是英國人管理)裡女性與孩童的長工時和惡劣工作環境,深惡痛絕。衛生狀況令人驚駭,母親在機間工作、小嬰兒就躺在走道上。」 ── 摘自《宋美齡新傳──風華絕代一夫人》第七章 |
![]()
關於蔣、宋結婚初期,坊間流傳許多故事,其中或許不少是穿鑿附會,但大多有事實根據。第一則故事發生在婚後幾星期,夫妻倆就吵架。根據蔣介石的日記,兩人在宋母家度過的耶誕夜「是我過去十年最快樂的一天」。可是,五天之後,日記出現:「我今天非常不快樂和孤單,因為三妹一氣之下走了,那是因為我沒自覺因她的頑固和火爆脾氣而冒起的粗魯反應……。晚上……我就迫不及待想見她。她覺得她生病是因為缺乏個人自由而起。她勸我要改改脾氣,我也答應了。」 美齡表明了她決心保持獨立自主、不是丈夫的附屬品,似乎是這個極端保守的儒家男子和非常不典型的中國新娘兩人之間時起勃谿的原因。一個月之後,她寫信給艾瑪說:她「不認為婚姻應該抹煞一個人的獨立自主。因此之故,我要做我自己,不是將軍之妻。這麼多年來我就是宋美齡,我認為我代表了某個意義,我也預備繼續發展我的獨立自主,保持我的身份。很自然,我丈夫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希望我認份當他的妻子;但是,我雖不說,還是決定要代表自己……。我要被承認是個因素(factor),因為我就是我、不是因為我湊巧是他妻子。」 第二個故事是蔣介石在日記裡寫道,美齡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即兩人婚後八個多月流產。蔣介石非常關心她,寫下:「她極端痛苦,難以形容。」但是,既無醫生(註1)、又無家人提到美齡有喜;加上蔣介石染過性病,美齡又動輒生病──真病假病、婦科病或其他病──我們很難相信這個事件不是捏造出來的。何況,蔣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陳潔如聲稱,他們婚後,蔣介石的醫生已告訴他今後無生育能力——這種事他恐怕絕不會向美齡承認,美齡若是知情,恐怕也不會嫁給他。 所謂的流產意外,歸咎到因為有人企圖行刺蔣介石,美齡受到驚嚇所致——這個故事又涉及美齡信及鬼神,「她相信受到上帝指引……有時候醒著、有時候在夢中」。她對一位朋友(註2)說:她把丈夫留在南京,回上海探視住院療養中的母親。她住在母親隔壁房間。幾天後,蔣介石也到上海,住在她房間隔壁另一寢室。蔣介石抵達當天夜裡,她夢見自己在房間外走廊走著,看到房裡自己一身白衣。有個兇神惡煞般的男子站在她房外,即將開門襲擊她,房裡的她趕緊鎖上門;可是,她還是看得到他。此人舉起雙手,各握一把手槍。她驚聲尖叫,這一叫吵醒蔣介石,他過來叫醒她。 次日上午,宋夫人要女兒和女婿回家。當天夜裡,美齡又做了一個夢。她和母親站在家裡的後花園,拿著一袋麵粉向地上灑一圈白色麵粉。白色麵粉圈中,裊裊出現一位白衣女子;雖然白衣女子形似觀音菩薩,卻一臉奸邪。她說:「我無事不通,可以為妳指點迷津。」看到母親示警的眼色,美齡問幽靈:妳是神、還是鬼?幽靈尖叫隱去,美齡也尖叫出聲。美齡醒過來,發現蔣介石在說夢話。他也醒了,兩人談了幾句,起身走出房間。他擊掌召喚衛士,結果出現兩名衛士、不是平常的一人。他有點納悶,但沒說話。 第三天夜裡美齡又做夢,夢見兩名男子潛身欺近她和蔣介石的寢室,意欲行刺。她尖叫、驚醒,發現蔣介石並沒在床上。她跑到走廊,發現蔣介石和一群警察在講話。警察在上午四點鐘前來敲門拜訪,及時阻止了刺客對他們夫婦的暗殺。兩名蔣介石平素信賴的衛士——現已上了手銬——前來意圖行刺。他們已經一連三夜企圖下手。第一天夜裡,他們已經即將欺近醫院蔣介石寢室門外,卻因她夢中尖叫,吵醒了蔣介石,只好作罷。第二天夜裡,他們又靠近寢室,因蔣介石說夢話而嚇壞,又因他召喚衛士,只好現身。第三天夜裡,其中一名衛士戴帽、並在制服之外罩上風衣,坐計程車到公館與另一名同夥會合。但是司機見其行跡可疑、向車行回報,車行通知警方。美齡因而相信,上帝透過她的奇異夢境,拯救了她們夫妻倆的性命。 第三個故事雖然可能出人命,還好結局尚可。蔣介石、宋結婚後約一個月,兩人回到上海。美齡顯然說服了蔣介石,既然已是中國最重要的人物,可以不必再像一般政府官員那樣,向杜月笙進貢保護費。他倆抵達兩小時後,蔣介石出門辦公。有一輛汽車登門,說奉命來接她去見「姊姊」。美齡在女傭陪伴下出門,但人一直沒到靄齡的家。 蔣介石數小時後回到家,發現她不見了,十分害怕。不過,他也明白「江湖道上規矩是不傷人」,遂打電話給內兄子文。子文再打電話給杜月笙,杜月笙告訴子文,蔣夫人「平安無事;她只帶了一名女傭在上海街上坐車閒逛,這樣很不安全;幸好他的手下發現,把她護送到一處安全的別墅,善加款待,但是她卻很不高興,不吃也不喝東西。」故事又說,杜月笙「歎息委員長太忙了,沒能好好安排自己和夫人的保護措施——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這是很要不得的缺失。」他建議子文到他家來,「一起安排確保他漂亮妹妹安全的措施,再陪她回到焦急的夫婿身邊。」子文匆匆趕到杜公館,交出保護費。他才得以帶美齡回到蔣介石身邊。 ……蔣介石復職後不久,與馮玉祥會商恢復北伐的計劃。蔣介石要親率第一集團軍;馮玉祥負責第二集團軍;山西省主席閻錫山領導第三集團軍;第四集團軍為預備隊,由李宗仁率領。國民革命軍的對手將是少帥張學良的東北軍,以及其他六個將領的部隊。攻勢預定在三個月後,即四月初發動。計劃安排妥當,蔣介石回上海。 沒有人比蔣介石更了解上海的誘惑力。即使日後在蔣介石生命中算是相當重要角色的史迪威,也同意上海是個很危險的城市。這個老古板的美國將軍在一九二二年初次抵達上海時就說:「這個城市很快就可以毀了一個人。在旅館門口搔首弄姿的女郎,使人不能不注意到她們。」蔣介石在校閱部隊後,對隊職官兵下達一道嚴格命令:嚴守紀律、不得惹事生非——別招惹「女郎」、也別碰政治。幾天之後,蔣介石發現約有五十名官兵曾在去年參與中共發起的反洋人暴動,他下令把他們統統就地正法、全部槍斃。這麼雷厲風行執法,目的不只是整飭軍紀,也是因為他要北伐、冒犯不起西方列強,因為他計劃要求他們不再以金錢、武器支援軍閥。他呼應孫中山生前的抱怨,宣稱:「去年中國內戰不休,是因為軍閥接受帝國主義者很大的支援。軍火彈藥源源不絕進入中國。大量金錢秘密貸借給我們敵人……。軍閥反抗革命軍,拉長了此一極為不幸的內戰。」 蔣介石要北伐,需要爭取更多錢支持國民革命軍。他和再度出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對上海銀行家和商界施加壓力,募到約一千五百萬元(註3)。子文說:「我們以令人痛心的大手筆花費把人員和金錢投入戰事,因為我們想以此為最後決戰。」但是,根據《北華捷報》的報導:「我們或許可以猜想得到,宋先生一定很痛心自己在過去幾個月扮演的角色,他對於用費毫無控制,卻要從企業界搾出巨額款項。企業界對此也必然十分厭倦。」然而,回顧起來,對這個題目夙有研究的專家柯博(Parks Coble)可能就不認同;他認為「宋子文以勸諭代替恫嚇,在過程中打造出銀行家和政府之間真正的同盟關係。」 蔣介石忙著各種公務,美齡則嘗試習慣她未曾接觸過的不同生活。雖然據她自己說,她的環境一向「優渥、舒服」,她仍做出大家意想不到的動作,搬到國民革命軍及國民黨中央所座落的總部南京去。美齡是破天荒、首開其例搬到南京住的高官夫人——別人都把家眷安置在上海。美齡是文、武領導人辦晚宴、接待會時的代表女性。「我想,官員們很注意我……但我慢慢就放輕鬆、忘了自己……。他們也開始不把我當女性、而當做是他們中之一員。」她也陪著蔣介石到處旅行。 「直到結婚之前,我從來沒住過那麼中式環境的空間。婚後我陪著委員長到各戰場,睡茅草屋、火車站或任何能找到的棲身處所。」 她說:「當時的南京不過是個小鄉下,只有一條所謂的大街……即使街道也很窄,兩輛汽車迎面相會,其中之一必須後退到另一條側街,才能讓對方先通過。房子都很原始、冷、不舒服。」美齡的評語,美國大使館助理海軍武官馬克修頗有同感。日後出任遠東情報頭子的馬克修說:「城裡沒有自來水或下水道系統。吹毛求疵的葡萄牙公使……抱怨說,他在南京要洗個澡,都得用瓶裝礦泉水。」 從上海有蒸氣供暖的華廈搬到南京冷冰冰的政府官舍,美齡似乎甘之若飴,承擔起領導人妻子的角色,主持黃埔軍校師生口裡的勵志社。勵志社原本是個年輕軍官接受政治教育的俱樂部。美齡在南京設立一個集會所,類似中式的軍官俱樂部——下了班後沒事幹的軍官可以在此放輕鬆、聽音樂、學畫,同時還可以幫助黨部製作宣傳海報。可是,在裡面他們不准吸菸、喝酒。美齡從基督教青年會找來黃仁霖擔任勵志社總幹事。 黃仁霖說:「原先只是一棟小小的矮房子,座落在一堆破舊房子當中。附近就是基督教青年會那棟漂亮的新會所。我承認留在基督教青年會的誘惑很大……但是我還是同意接任新職……。許多軍校幹部對我們有成見,認為勵志社是一種新的外國宣傳方式,隱藏著要強迫他們改信基督教的用心。我走在路上,他們會朝我丟東西……。但是,慢慢地,他們開始喜歡進來,利用設施。現在,所有的軍官都加入了。」 這些軍人並沒錯——勵志社是道道地地的新式宣傳工具,不過不是外來、而是本土的,企圖把革命推到軍官的心靈之中。蔣介石追求一位有錢有勢的妻室,得到一位兼具構想和精力的女性。 【註1】根據狄隆(Thomas Delong)說法,醫生告訴美齡,她並沒懷孕。 ── 摘自《宋美齡新傳──風華絕代一夫人》第十七章 |
![]()
魯斯兄妹形容結婚前的靄齡「永遠不停在喬事情」。靄齡建議慶齡接替她,擔任孫文的秘書。不論是否知道她這樣做的後果,它勢必使得年輕、理想、沉浸在革命熱情的慶齡對革命之父產生感情。慶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給小妹美齡的信上說:「我可以幫助中國,我也可以幫助孫博士。他需要我。」孫文教導慶齡如何解讀密碼信件、用隱形墨水寫信這兩門地下政治工作者的技巧。他也教她精確時,以及如何察覺政府間諜。 他們倆剛在一起的時候,孫文處於情緒的低潮。他被袁世凱打敗,自信心嚴重受創,也損及無私無我之心,他不再相信同志,而且生平第一次自怨自艾。被逐出統治集團,使孫文自覺卑微,憤怒怨懟。他怪罪國際銀行團害他敗給袁世凱,「不是我們自已人、不是我們本身的錯害我們逃離中國,而是外國金權,刻意分裂我們國家。五國銀行團控制住南、北權力平衡達三年之久。當我們主政時,他們逼我們接受最羞辱條件,否則就不貸款……。去年給予袁世凱的個人貸款……授予北方一根巨棍粉碎我們的革命。這筆巨大賄款,造成我們今天流落到這裡。」 宋慶齡對孫文理想的敬愛,化為對他本人的迷戀,孫文對她產生情愫也不難想像。孫文的婚事本來就是奉父母之命,還在讀書時就和沒受過教育的妻子成婚,婚後兩人聚少離多。他想娶靄齡所遭到的峻拒也有傷自尊。現在,孫文已年近五旬,天天和一個美麗、受過良好教育、二十歲妙齡、而且又崇拜他的理想和本人的女子相處,一個從榮耀巔峰跌下來的男人,還能到哪裡去找尋慰藉? 關於孫文和宋慶齡結婚的故事有許多版本。綜合起來,情況大致如下: 宋慶齡向住在日本的雙親報告,她要嫁給孫文。他們嚇壞了。不僅因為兩人年紀相差近三十歲,還因為宋家和孫家都是基督徒,而基督徒不像一般中國人,是堅守一夫一妻制的。即使中國人並不信基督,他們的婚事要由長輩提親,也不是當事人自己提。而且,男子要討第二房太太,也要雙方家庭同意。 在中國,婚姻未必和愛情或迷戀有關。男女結合是兩個家庭為雙方利益而結合,生兒育女是為了傳宗接代、照料祖墳。子女自己選擇婚配對象,對傳統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言,根本就是離經叛道。雖然宋嘉樹養育女兒,要她們受教育、有主見,但還是有些界線是不能跨越的。在中國,家庭的福祉和聲譽超過成員的福祉和聲譽;有位作者就說:「中國家庭愈大、愈有權勢,其成員就愈脫離不了桎梏。」這個信念的核心就是孝道。父親在家裡就像皇帝,是最高的權威,不能被冒犯,甚至不能拿不愉快的真相去干擾他。 因此,宋嘉樹一覺得安全無虞,立刻全家搬回上海,也就不足為奇了。宋慶齡不肯嫁給一個年輕、合適的對象,就被父親禁閉在家。但是,慶齡若是屈服,就不是宋嘉樹的女兒了。她背著父母親發了一封信給孫文,問他該不該回日本。孫回信表示需要她,她就逃家了。 宋慶齡後來告訴美國作家史諾(Edgar Snow)說:「我沒有墜入情網。它是一種英雄崇拜。當我逃家去為他工作時是一種羅曼蒂克的女孩想法--好的想法。我想要幫助救國、孫博士是可以救國的人,因此我要幫助他。我從衛斯理安回國途中,前往他流亡的日本探望他,請纓服務。他不久就傳話到上海給我,說需要我到日本幫忙。我父母親不同意,想把我關起來。我在女傭協助下爬窗逃家。」她立刻前往日本--這是一項大膽舉動、一種違背衛理公會宗教的罪行,也違背了宋家的道德規範。她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抵達日本。孫文體會到讓她在這種情況下回到日本,易遭流言中傷,同時安排妥當和元配夫人的「離婚」手續。 宋慶齡告訴史諾:「我在抵達之前不曉得他辦了離婚手續、也打算和我結婚。當他說明他怕我會被人稱做是他的小妾,而且醜聞會傷害革命,我就答應了。我從來沒有後悔過。」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們倆在她抵達日本的次日,就在一位日本名律師家結婚。雙方家人均未出席婚禮。 孫、宋聯婚的新聞事隔三個月才傳出--首先經過日本報紙披露,旋即傅遍海外。史諾認為孫文的「離婚手續含含糊糊」,意在防堵眾口悠悠的批評,顯然也未達成效果。中國基督徒拒絕接受宋慶齡是孫文合法妻室的事實;兩人成婚後,各教會不再邀孫出席演講,教會刊物也不再把他列為中國基督徒的表率人物。 用不著說,宋氏家族的反應要比一般基督徒更加激烈。慶齡的母親是極為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她嚇壞了;宋嘉樹設法要帶她回家。她對一位傳記作家說:「我母親一直哭,我父親已染肝病仍然抱病前來求情……雖然非常對不起雙親--我也痛哭流涕--我拒絕離開丈夫。」她也告訴史諾:「我父親來到日本,痛斥孫博士。他試圖以我尚未成年、未取得父母親同意為理由,使婚約失效。但是,他沒能成功,遂與孫博士絕交,也和我斷絕父女關係!」 ── 摘自《宋美齡新傳──風華絕代一夫人》第六章 |

 1897年,宋美齡生在上海,父親宋嘉樹自幼赴美謀生,得貴人相助受神學訓練,之後回中國傳教,以印製聖經、經商致富。
1897年,宋美齡生在上海,父親宋嘉樹自幼赴美謀生,得貴人相助受神學訓練,之後回中國傳教,以印製聖經、經商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