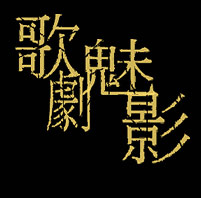


| 一九九三年夏天,我在倫敦女王戲院觀賞了嚮往已久的《歌劇魅影》,秋天又有小說中譯本先睹為快的機會,套句文藝腔說辭,我真是陷身於喜悅與恐怖的氛圍中。從前我恐怕是被唱片裡麥可克勞佛甜美的嗓音給哄騙了。直到看過歌劇和原著小說以後,才真正嚐到卡斯頓.勒胡在蜂蜜裡下的膽汁。 |
勒胡生來就是寫黑色推理的料,一八六八年他母親在回諾曼第的路上碰上交通阻塞,竟因急產臨時將他生在巴黎一家棺材店裡。勒胡二十一歲那年繼承了父親一筆百萬遺產,在巴黎河左岸和拉丁區,過著香檳與乳酪一般的好日子。他學的雖是法律,卻沒有專心朝老本行發展,反而在新聞和雜誌界打零工,當起逍遙的特約撰述。勒胡生性愛旅行,在近二十年的記者生涯中,幾乎跑遍全世界,這些豐富的奇風異俗閱歷,日後都在他的小說中伸枝冒芽。 勒胡在三十九歲那年感到倦勤,掛掉一個清晨三點的電話 主編要他即刻搭火車去法國南部採訪一樁戰役,決定在巴黎當一個蝸居的小說家。直到五十九歲那年逝於尿毒,他一共完成六十二篇小說.果然敬業又樂業。 一九一一年勒胡出版了《歌劇魅影》,這部作品對也的寫作生涯意義非比尋常。在撰寫一大堆床頭小說後,他自覺需要有那麼一本小說,能讓「卡斯頓.勒胡」這個名號,起碼在文學史上佔一個小角落。 這本寫得特別花力氣的小說,沒想到賣座反而沒有預期中的好,一直到十四年後,好萊塢將它拍為默片.捧紅了大明星隆錢尼,這本小說才順勢推舟大大暢銷。對命在旦夕的勒胡,雖然是一劑回天乏術的強心劑,但風燭殘終還能發覺自己的確押對了寶,足可含笑駕鶴了。然而文學史是人間最無情的榜單,等到一九八二年作曲家安德魯.韋伯靈機一動,想改編此書為歌舞劇時,勒胡的小說不只早從書店下架,也幾乎絕跡於書市了。韋伯只好委託舊書商幫他在千鍾之中,找到這微渺的一粟。說也奇怪.勒胡的小說再一次鹹魚翻身,韋伯的歌舞劇在全世界各大都會連演數年不墜,唱片也一再衝破白金大關,小說當然也水漲船高。這就是在書「名不見文學經傳」卻在出版後的八十二年,會有中譯本問世的由來。 |
到底這是怎樣的一本書呢?套句現今專家學者愛用的「類型」說法,它是愛倫坡加上柯南道爾。勒胡自己也提過,生平最服膺的便是這兩位作家前輩。如果再加上巴黎那時還瀰漫著的「雨果風」,《鐘樓怪人》對本書氛圍的啟迪,就更完整了。簡單說來,它是描述歌劇院鬧鬼,鬼魅囚禁紅伶強行求歡,愛人前往搭救的冒險故事。如果小說也有「配色」這本書就具備大紅與大黑的反差,故事周旋於水晶燈下的豪華劇場,以及暗無天日的地下儲藏密室。當它搬到倫敦女王戲院的舞台上時.難怪視覺效果那般優異。 雖然小說情節撲朔迷離,但勒胡將它視為記實的情節,在作品中以「我」的角色抽絲剝繭,一再證明這是一則真的故事。當讀者巡訪倫敦時,絕不忘去貝克街二二一號看「福爾摩斯的房子」,天曉得柯南道爾寫作當年才只編到一百號;而歌劇迷進入巴黎歌劇院時,一定也要去敲敲二樓五號包廂的大理石枉,看它是否空心,曾經容下鬼魅藏身。沒有人曉得,為何勒胡對巴黎歌劇院的密室,知道的那麼詳細,他簡直就是神出鬼沒的艾瑞克的化身。當韋柏和他的歌劇製作班底,為舞台設計而親訪巴黎歌劇院實景勘察實,才發現勒胡對歌劇院的描寫,並不是憑空捏造的,而萬分感佩這本小說的寫實度。 |
勒胡的創作動機,也起始於一八九六年歌劇院大吊燈無端墬下砸死人的真實新聞事件。閱讀這本小說最大的樂趣,辨識追蹤真與幻的交纏糾葛。勒胡不斷「用愛倫坡來打結」,然後在「以柯南道爾來解套」。艾瑞克被描寫成走遍大將南北,再俄羅斯、蘇丹、波斯學過各種馬戲魔術、腹語、機關模型的異人,建築和音樂是他最拿手的老本行。他在小說中,幾乎扮演「全知觀點」的,但微妙的是,作者再描寫他的言行舉止時,又只能不斷猜側。 電影和電視後來製作了幾齣艾瑞克的故事,但都與小說情節有所出入。因為敘事觀點的改變,或是魅影身世的描繪,反而讓情節過於窄化。再勒胡的小說裡,艾瑞克這個「人」簡直不是固體的,他幾乎只是一股氣,真正存在的東西是他的黑披風。讀完整本小說後,你簡直說不出他像浮士德呢?還是更像梅菲斯特?但克麗絲汀無疑的會是馬格麗特。雖然我也極喜愛韋伯的歌舞劇,他安排劇中人出現在舞台框架之外,以及用頻仍的換景不斷展現出劇場的豐富面,但在人物心理的挖掘上,與原著比較是瞠乎其後的。 雖然這是一齣歌劇院為藍本的小說,但書中並沒有太多專業的術語,除了少數一些人名和劇名外,不會影響閱讀順暢。如果要說它和歌劇有些什麼呼應,那卡斯頓•勒胡已掌握十九世紀法國浪漫大歌劇的精隨,那就是誇飾與排場。再觀眾相繼離席後,豪華的水晶吊燈仍兀自堅持著,它要自己在暗地裡發光,真像是這本被遺忘又被紀起的黑色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