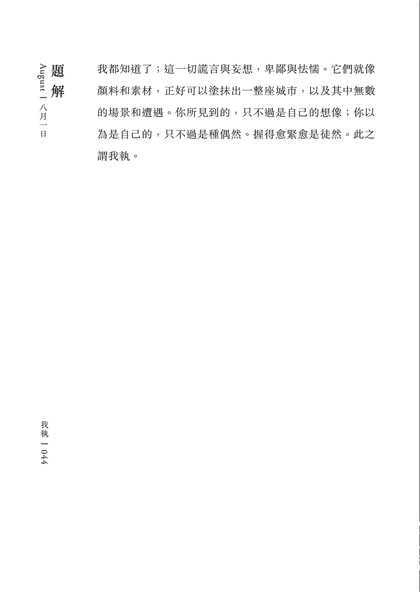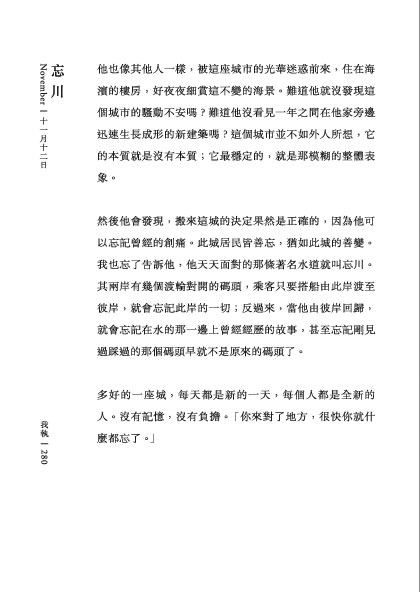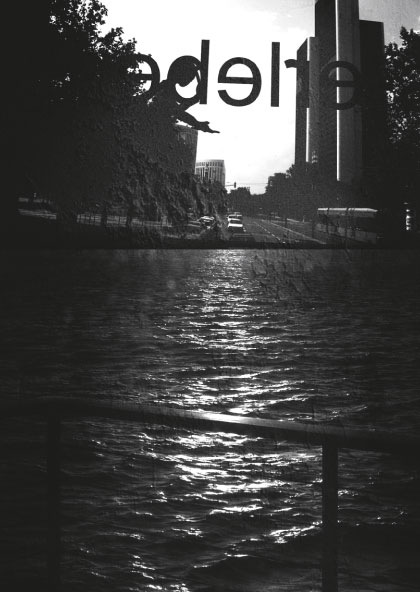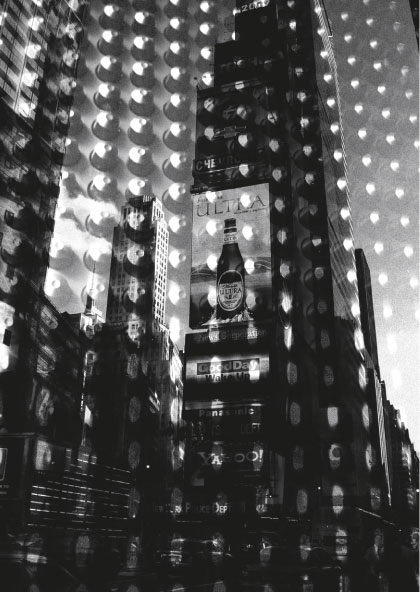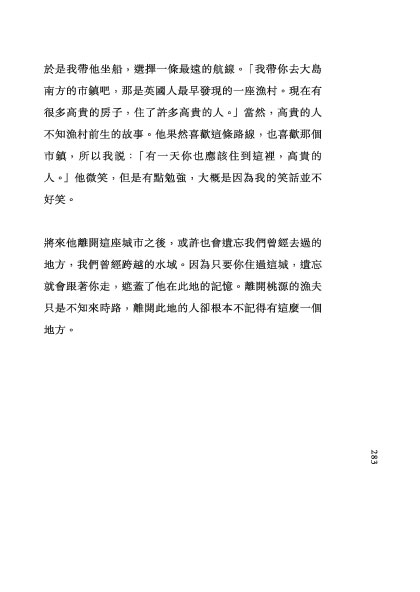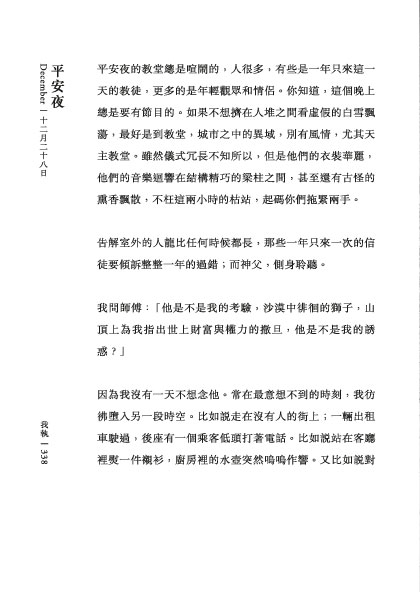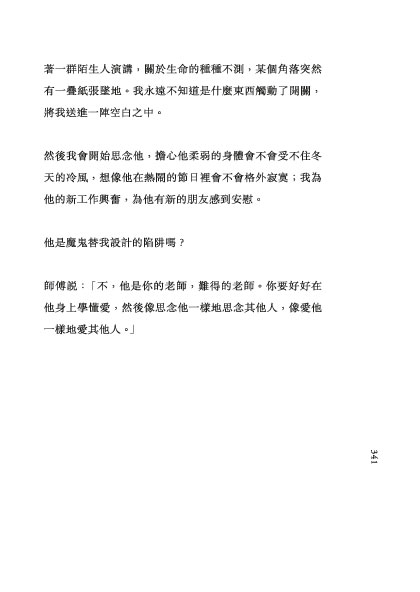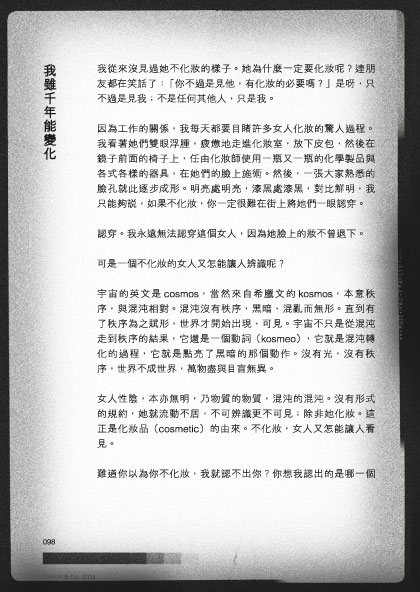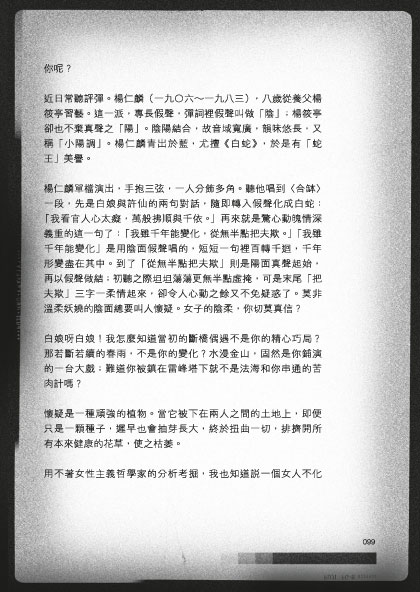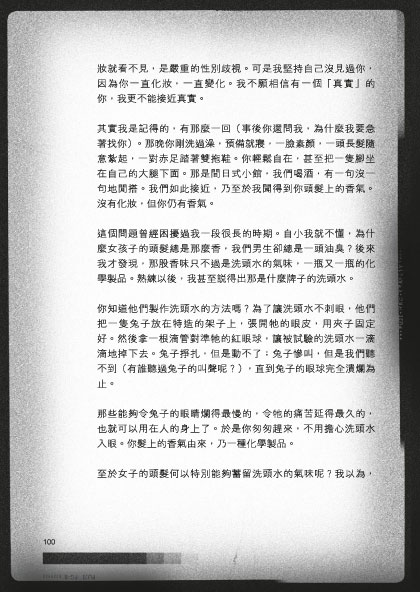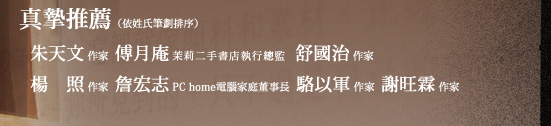

 |
||
| 梁文道 著 平裝352頁 ※ 封面特色:英文書名燙銀色、打凸,中文書名上局光 定價350元 特價276元
|
 |
我都知道了;這一切謊言與妄想,卑鄙與怯懦。 它們就像顏料和素材,正好可以塗抹出一整座城市,以及其中無數的場景和遭遇。 你所見到的,只不過是自己的想像; 你以為是自己的,只不過是種偶然。 握得越緊越是徒然。此之謂我執。 —— 梁文道 |
本書為華人世界最耀眼的公共知識份子、評論員、書評人的梁文道所撰寫的散文隨筆集,拋卻了一向給人理性自持、睿智犀利的一面,反將他的私密事,包括內心難以排解的焦慮、軟弱、甚至人際的摩擦都披露出來。書裡談及愛情、日常生活、疾病經歷、信仰感悟、城市文化、文學藝術、歷史記憶等個人生活體驗和人生感受等諸多方面。 誠如作家楊照所言,《我執》一書「與其說是梁文道私人生活的祕密,還不如說是一種祕密的閱讀態度」,讀者不但可以「藉由那似幻似真、既事實又虛構的筆法,讚歎這位讀書人的閱讀興味與閱讀能量」,還能「把閱讀內容轉化成自我體驗,豐富我們的私密自我空間」。 名人的真摯推薦 當然是我執,否則我們來此一世所為何事,否則我不生今世又生何世?逐物迷己,我們在好聽的鷓鴣聲裡迷了己。還有,此書要跟梁文道的另一本書《常識》並看。《常識》裡梁文道鮮明的公共知識份子的位置,面對大眾民粹仍不懼於講複雜的語言和觀念,衡諸當下台灣,南方朔算是,唐諾是,而梁文道比他們都年輕又正在發揮影響力。把《我執》放在這個瀕臨絕種的位置上來讀時,它的徘徊隱爍,它的抒情性,立即翻轉出異樣的風致。 都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沙漠裡卻長出了大樹。如今華人世界最耀眼的公共知識份子、評論員、書評人,自非香港梁文道莫屬了。他讀書也說書,評今又論古,喋喋不休卻針針見血,像把溫柔的刀,讓人一見一聽便難忘。恣肆之洋常有個平垠之底,破革之箭多射自柔軟之弦。人間有情,愛憎纏縛;纏縛不斷,慧命增長。文道有惑,心事難解。破惑解心偏多情的種種焦慮,日夜擣鑄,遂成就了大好一本書,名曰《我執》。 香港有個梁文道,他寫文章、論時情、觀看世界皆有獨造。我禁不住好奇他是怎麼做到的,同時也佩服有人能做得那出色、那麼妙。 《我執》寫的,正是一種極度強烈的「有我」的文學;《我執》記錄的,正是唯有透過這種「有我之境」才會出現的奇異景致。雖然一開頭八月一日的〈題解〉文中說:「你以為是自己的,只不過是種偶然。握得愈緊愈是徒然。此之謂我執。」然而放在閱讀與文學的範圍中,「徒然」非但不是「徒然」,反而要從「徒然」中、從對於「徒然」的虛無慨嘆中,才有辦法燦然冒生出值得被領略記取的光彩來。 梁文道是當今華人世界特立獨行的知識份子,自由出入雅與俗,能闡述理論,又能感悟大眾,極少見集思想者、議論者、行動者於一身的人。《我執》這本奇書,他自己說是追隨羅蘭.巴特《戀人絮語》的體例,我卻看見法國知識份子更久長的《沉思錄》傳統,難得一見有趣的書。 像一個廢園裡的日晷,生鏽的、遺忘的什麼。這很像梁文道在夢境的鬚根猶附著靈魂灰稠時分的譫言絮語,與平日雄辯、機鋒、公共論述話語的他如此不同,我們看見一個哀感、憂鬱、徬徨的自畫像。 彷彿現代版的《一千零一夜》,說故事的人藉著說故事得以延續生命,但梁文道卻藉著說故事,通過藝術的手段,以文字責要哲學意念,試圖修鍊自我,使之肉身和精神都臻於昇華。 |
- Top -
1970年生於香港,在台灣成長,1985年回港升學,1994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梁文道長年參與各種文化、藝術、教育與媒體工作,並熱心支持多樣化的社會運動。他曾任多個非政府組織及藝術團體董事或主席,牛棚書院院長、香港商業電台一台總監,以及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的客席講師。現為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 自1988年開始,他在報刊發表劇評、樂評、影評、書評,以及文化和政治評論。目前在中國大陸《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上海書評》、《東方企業家》、《天下美食》,香港的《蘋果日報》、《明報》、《飲食男女》、《AM730》、《讀書好》,台灣《聯合報》,馬來西亞的《星州日報》與《亞洲眼》,以及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等報刊上均可看見他的作品和專欄。嘗出版書話《弱水三千》和《讀者》,飲食散文《味覺現象學》,電影和音樂札記《噪音太多》,以及《十二》和《我執》等兩部散文集與訪談錄《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其時事評論集《常識》不但在大陸創下出版三個月內銷售十八萬冊的佳績,更榮獲中國大陸2009年十大好書。 他被認為是當今中國大陸和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曾獲《Esquire》大陸版評選為「Men of the Year之2008年度意見領袖」等多種榮譽;並得到中國大陸《出版人》雜誌所頒發的2009年度作家。 自2009年十月份起,台灣《聯合報副刊》也邀請梁文道撰寫【懷念書】專欄。 梁文道談《我執》 至於《我執》,我把它當成是一趟清理自我問題的療程。當然,積壓了這麼多年的疑惑,不可期待畢其功於一役。如果它有點感傷,也許是因為我有時候真的很感傷,於是把我讀到的一切讀進感傷;又或許是因為我讀到了很感傷的東西,不得不把自己整個人都讀進去,就像小時候看瓊瑤,你非把自己想像成是個患上末期癌症的貧家子不可。如此鋪衍,這個我就只能不斷蔓延擴大了。說來說去都是我,這不是「我執」是什麼?(引自本書「自序」) |
- Top -
香港有個梁文道
終於,我被出版社委託談一談他。然我實知他不多,雖我識他亦有十來年。只不過其間沒機會見上幾面,但每回見面卻又聊得極愉快極豐富。 但我真不夠資格談他。先別說我的學問不夠;再者我看不到他的電視節目(台灣看不到鳳凰台,說來不怕人笑,舍下亦無電視);三者不諳電腦,讀不了他在網路上與日俱增的文章;甚至他在書上報上的文章我竟也忘了去追來細讀。光陰似箭,轉眼間他已從二十六歲的昔日少年馬上步入四十歲的壯年矣,也已文章寫出了、電視上論出了恁多各題各類各趣各風的作品,開啟了恁大的一片思想與知識之文化論窺事業,這一下子,我忽然好想多曉得他一點了。我,也開始強烈的好奇了,好奇怎麼會形成這樣的一個獨樹一幟、自闢蹊徑的年輕學問家的? 於是我便在紙上寫下:香港有個梁文道……… 當然,我雖好奇,卻並不深悉他的成長與治學等諸多實情,只好就我在與他七八次的香港、台北、與北京的酒飯席間晤見上來揣想一個可能的梁文道。 譬似他永遠在看書看書看書,看了這本,還要看那本,看了文學的哲學的,還要看歷史的政治的,世間每一種事象皆不願放過,皆極有興趣。更還不只是興趣,是不累。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莫非是一股童心?一股追問?莫非是一種對父親、祖父,甚至舅舅、表哥等的殷殷追隨與跟從,企求自他們大人那兒得到即令是出海冒險的快樂卻同時仍獲有依仗的保護與溫暖,以及愛。 他這種不歇的好奇心,或說糾纏不休的窺探,幾乎已像是在萬里尋親的途中不放過任何遭逢親人的窄縫機會。 幾乎可以說,他有一種傻,這種傻,這種專情,教他做恁多的事而不感到累。一如兒童的嬉戲瘋鬧。又他的傻,是一種渾然天真,你今天和他碰面,聽他說話或看他聽人說話的反應,覺得天真純樸,並不如何如何聰明,但明天你看到報紙上他的文章,奇怪,怎麼比昨天多聰明了點呢?再過幾天你看到電視上的他,他媽的,怎麼又更聰明了呢?梁文道便是這麼一個不即時露出他犀利才智、卻始終與日推移左右逢源目送飛鴻手揮琵琶的獲取他更深化學養與淬鍊慧根的「學問栽植家」。並且他隨手拈來。這亦是他生活與工作的高明處與獨特處。 怎麼說呢? 他看似只工作(寫稿、讀書、上電視做節目),不生活;然看自他的文章與節目,充滿了生活的各樁情節:伊斯坦堡的海峽、京都的百年旅館、亨利.詹姆斯的情感、少年台灣小太保的荒好歲月、生牡蠣的腥香鮮甜。 其實他抓緊片段的空閒,瘋烈的生活。譬似這兩年我遇見的他,常在飯桌上,他抓緊與同桌六、七人多聊、多聽彼此近況,也同時迸發撞碰新出的任何話題,常常有趣極了,也熱鬧極了。這便是他的獨妙生活,也是他特殊修士般工作下的極佳娛樂。然後九點半十點飯席散了,他馬上又要回到幽禁如武俠小說面壁石洞的旅館房間去進行三到五個小時(有時甚至到天亮)的無人窺知的默默寫作自懲。(「鏘鏘三人行」掌櫃竇文濤說得好:「文道寫稿量與讀書量的大,與睡覺量的少,幾乎是自虐」)。 正因為他太常在室內檯燈下伏案,致他說及的外間,皆是極如嬰兒初見的光亮明潔、花也香海也藍的興奮。這種封閉式的工作型態,造就了他的天真,也達成了他的與世俗之隔絕。但他不能在光風霽月下待停太久。說來好笑,我差不多已在遐想,若梁文道在百忙中到台北休假三天,啥事也不用做,那我可以怎麼替他規劃一個行程呢?我甚至想,我自己亦可不留在台北相陪,歡迎他住我家客房,每天自顧自出門遊玩,我寫好幾張A4紙的可遊可逛行蹤,何處不妨小坐,主人可略談,何處院子花好,何處咖啡好,何處人景佳,何巷黃昏時分光好,他自去玩,他自去吃,他自徜徉與歇腳。 甚至台東,亦可如此規劃與他。便為了或許令他享三天實則平常之極的清福。
他像是太愛這個社會,故而要去離開。他像是太愛這些人群,故才不與他們靠得太近。就像電影或小說中的傑出兒子,太愛他的媽媽、姊姊、弟弟,便只能躲在樹後看著他們、保護他們,卻不與他們見面;乃相見只益增得悉他們脆弱後生出的不忍。 於是他消除不忍不捨的心底之痛,只好一逕的寫、一逕的說,教人們一點一滴的從不同的角度逐步知解生命。譬似少寫了一篇文章便少誦了一堂經般的令眾生的苦痛沒得到立解。 他的業作,我東思西想除了說「僧道一流」,已無其他身份可以解釋。有人謂他是意見領袖,實他無意做任何的領袖,只是想找出意見、講出意見。在這一處講完了意見,便再去另處繼續尋找。意見是他優遊人生的最佳故鄉,但也頂多如此,他只誦經,不做方丈。(本文同步發表於2010-01-07《聯合報副刊》) |
- Top -
「有我之境」的私密閱讀 我將梁文道的《我執》看作一本極其獨特亦極其深刻的讀書筆記。 不只因為梁文道是個認真、傑出的讀書人,而且他在書中明白警告: 「如果一個人受過嚴格的文學理論訓練,對於亨利.詹姆斯的小說是為了補償自己對女人的虧欠這種說法,應該是要嗤之以鼻的。因為根據理論提供的常識,作者的實際生活和他筆下的作品不可能有這麼簡單直接的關係。假如有關係的話,那也是可疑可議的。」 換句話說,《我執》的內容不可以、不應該簡單地被視為:二○○六年下半年,梁文道遭遇了生活上,尤其是愛情關係上的挫折,有一個「他」突然從梁文道的居住之處離開消失了,而這些片段小語,就是那樣挫折痛苦思念心情下的靈光紀錄。
「可疑可議」之處,無法立即揭露,還好文章裡留下了其他不那麼可疑、不那麼可議的線索,可供做為依據。那就是書中大量引用的其他文本。 不管那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敘述者,是梁文道還是虛構的角色,還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某種扭曲變形或精神原型,文章裡讀著書、記錄著閱讀反思的,總是不折不扣,我們平常認識的那個梁文道。 在二○○六年八月到十二月間,他讀了《戀人絮語》、《貓河》、康拉德的傳記、《魂斷威尼斯》、《禁錮在德黑蘭的羅麗塔》、Edward Hopper的畫、《空間詩學》、《紙房子》、《生活與命運》、《書簡三疊》……等等、等等。他的生活、他的經驗,由這些閱讀堆砌構築而成。 前面引用的那段文章,出自九月十三日的〈借用〉。有趣的是,「借用」有兩方,借方與貸方,然而在生命與閱讀的關係裡,究竟孰是借方孰是貸方呢? 我們平常習慣的想像,是生命借用閱讀。生命中有了什麼樣的感受感懷,我們自己說之不足道之不完,於是將前人在書中講過的話,借來運用,說:「啊,我也正有此感!」或「啊,他已經幫我講得如此精確!」或「啊,今天我才懂了書中的意思!」 然而,會不會存在另一種反向的可能,是閱讀借用生命?甚至:為了彰示、擴充閱讀的領略,才不得不借用具體生命故事來做為映襯、基底? 我懷疑,而且我覺得有充分理由懷疑,《我執》正是這種反向「借用」的精彩示範展現。一個讀書人,因其傑出且強大的閱讀能力,感應了藏在書籍文本後面的人間情緒矛盾糾結,穿透知性的理解而碰觸到了直覺感受,他沒有辦法繼續訴諸理性文字來傳遞那感知情緒,或者該說:那樣的感知情緒一旦被寫成理性文字就失去感染力量了,這種閱讀需要一個主觀且情緒性的主體做為橋樑來傳達,於是梁文道就借用了一個主體生命,似幻似真、既事實又虛構的敘述者,來撰寫這樣一部奇特的讀書筆記。
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生命,理所當然開放了所有感官的敏銳,迎接並對抗這個世界,於是他自己成了一面多角稜鏡,將通過他的平常混濁的光,折射成鮮麗得令人無法逼視的純粹色彩。 換個方式說,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生命,就是有著最強烈「我執」的生命。挫折痛苦思念來自於「想不開」,來自於清楚意識自我「自性」,所以會沉耽在離去、喪失以及想要追悔回復的掙扎中。這是最「有我」的生命。 《我執》寫的,正是一種極度強烈的「有我」的文學;《我執》記錄的,正是唯有透過這種「有我之境」才會出現的奇異景致。雖然一開頭八月一日的〈題解〉文中說:「你以為是自己的,只不過是種偶然。握得愈緊愈是徒然。此之謂我執。」然而放在閱讀與文學的範圍中,「徒然」非但不是「徒然」,反而要從「徒然」中、從對於「徒然」的虛無慨嘆中,才有辦法燦然冒生出值得被領略記取的光彩來。 這批文章最早在香港報章刊載時,專欄題記為「祕學筆記」,內中所藏的,與其說是梁文道私人生活的祕密,還不如說是一種祕密的閱讀態度。不是平常會在文章或錄影上看到的那種公共態度,不是分析歸納或排比解說的態度,而是一種穿過具體生命,「我」無時不在、主觀、感性、乃至於高度情緒化的私人態度。「祕學」者,是「私密之學」的意思吧! 我們不必試圖從《我執》的文字裡,去破解梁文道的私生活,不過我們卻可以藉由那似幻似真、既事實又虛構的筆法,讚歎這位讀書人的閱讀興味與閱讀能量,他當然能解析字面的普遍、公共意義,他還能進而和作者和文本進行生命與生命覿面相見、赤裸私密的感應,把閱讀內容轉化成自我體驗,再用半告白半反思的語氣,鑽入每位讀者的生命中,豐富我們的私密自我空間。 |
- Top -
八月二日 九月十六日 十月二十四日 十一月八日 十二月八日
十一月十二日 忘川(1)
十一月十二日 忘川(2)
十二月二十八日 平安夜(1)
十二月二十八日 平安夜(2)
我雖千年能變化(1)
我雖千年能變化(2)
→ 看更多試閱內容 |
- Top -
華人世界的「文化教父」梁文道,來到台灣了!作家好友張大春、駱以軍與張鐵志應遠流之邀「談文說道」,細說他們所認識的梁文道——他的才情、視野、氣度,更多的是他的真性情。梁文道更親自為台灣讀者說說自己《我執》內心細密的思維與情感。 〔第一場〕閱讀世界•閱讀自己──梁文道與張大春的Men’s Talk 時 間:2010年1月31日(日)下午17:40∼18:40 〔第二場〕談文道人──與《我執》作家梁文道面對面 時 間:2010年2月6日(六)下午14:00∼15:30 〔全球華人作家會〕香港文壇名家談在香港寫作的樂趣與困境 時 間:2010年1月30日(六)下午17:40∼18:40 〔經典3.0 名家演講活動〕永遠謳歌思考──讀 馬可奧勒留《沈思錄》 時 間:2010年1月31日(日)上午11:00∼12:30 |
- Top -


 梁文道
梁文道 香港有個梁文道,他寫文章、論時情、觀看世界皆有獨造。我禁不住好奇他是怎麼做到的,同時也佩服有人能做得那麼出色、那麼妙。
香港有個梁文道,他寫文章、論時情、觀看世界皆有獨造。我禁不住好奇他是怎麼做到的,同時也佩服有人能做得那麼出色、那麼妙。 梁文道說話,沒有廣東腔。這與他童年待過台灣有些關係。但更與他喜歡接近所有的風土、所有的異地有關。而他雖每日寫稿一如太多香港寫家在報上所作,但奇怪,他的議論與絕大多數的「港見」極不相同。這三十年太多的香港專欄文家,即使見多識廣,留英留美,談英談美,高論不乏,但總還是流溢著濃郁的港見,更不時透露出某些港嘆。這頗正常,亦很應當。然而梁文道小小年紀,何以比較少這些東西呢?梁文道議港談港,必也不少,只不過他所在意的「居港思港」之念,或許疏談得多。搞不好他看任何的中國人角落,不管是新加坡台灣香港,鬧熱哄哄珠江三角洲、吳儂甜軟的江南,喳喳唬唬的北京、擺龍門陣的四川,皆以某種類似遙遠卻又好奇的眼光。梁文道身處其中,似不很投入,就像他自己並不嵌在裡頭,這種「自火車上探頭看一眼」式的觀察,卻寫出、談出極其精闢的論見,是他的絕活。何也?哦,是了,是舉世皆過度世俗了。而他即使每一天皆投入世俗,卻怎麼也沒與他們一般的世俗。中國大陸的一忽兒大鍋飯又一忽兒全民奔經濟,香港的商樓滿佈、逼人透不過氣的金融競逐,台灣的人人顧盼自雄、皆欲自做老闆、政治見解滿口、儼然有朝一日亦想登高從政………他皆很能樂知樂見樂聽樂參與其中實況,並享受眾人的喧囂與野悍暢肆,但他究竟是梁文道,一個埋頭伏案的書呆子,一個只知理出思路的哲學探索者,一個若即若離的旁人;這些事皆不受他染指,這些地方即使他皆深愛卻都不是他的故鄉,他像是住在寺院裡。
梁文道說話,沒有廣東腔。這與他童年待過台灣有些關係。但更與他喜歡接近所有的風土、所有的異地有關。而他雖每日寫稿一如太多香港寫家在報上所作,但奇怪,他的議論與絕大多數的「港見」極不相同。這三十年太多的香港專欄文家,即使見多識廣,留英留美,談英談美,高論不乏,但總還是流溢著濃郁的港見,更不時透露出某些港嘆。這頗正常,亦很應當。然而梁文道小小年紀,何以比較少這些東西呢?梁文道議港談港,必也不少,只不過他所在意的「居港思港」之念,或許疏談得多。搞不好他看任何的中國人角落,不管是新加坡台灣香港,鬧熱哄哄珠江三角洲、吳儂甜軟的江南,喳喳唬唬的北京、擺龍門陣的四川,皆以某種類似遙遠卻又好奇的眼光。梁文道身處其中,似不很投入,就像他自己並不嵌在裡頭,這種「自火車上探頭看一眼」式的觀察,卻寫出、談出極其精闢的論見,是他的絕活。何也?哦,是了,是舉世皆過度世俗了。而他即使每一天皆投入世俗,卻怎麼也沒與他們一般的世俗。中國大陸的一忽兒大鍋飯又一忽兒全民奔經濟,香港的商樓滿佈、逼人透不過氣的金融競逐,台灣的人人顧盼自雄、皆欲自做老闆、政治見解滿口、儼然有朝一日亦想登高從政………他皆很能樂知樂見樂聽樂參與其中實況,並享受眾人的喧囂與野悍暢肆,但他究竟是梁文道,一個埋頭伏案的書呆子,一個只知理出思路的哲學探索者,一個若即若離的旁人;這些事皆不受他染指,這些地方即使他皆深愛卻都不是他的故鄉,他像是住在寺院裡。 不,如此看待這批文章,太直接太簡單,缺少了認真閱讀文學作品所需要的複雜「可疑可議」態度。梁文道和那個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敘述者之間,不能如此直接簡單等同起來,而該有著其他「可疑可議」的關係。
不,如此看待這批文章,太直接太簡單,缺少了認真閱讀文學作品所需要的複雜「可疑可議」態度。梁文道和那個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敘述者之間,不能如此直接簡單等同起來,而該有著其他「可疑可議」的關係。 書中的敘述者不是剛好失戀,所以借用《戀人絮語》;反而是只有透過主體失戀的經驗才能深刻傳遞閱讀《戀人絮語》的感動,於是那位敘述者就非失戀不可了!
書中的敘述者不是剛好失戀,所以借用《戀人絮語》;反而是只有透過主體失戀的經驗才能深刻傳遞閱讀《戀人絮語》的感動,於是那位敘述者就非失戀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