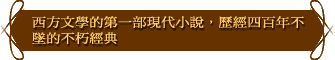
德國詩人海涅推崇塞萬提斯、莎士比亞與歌德三足鼎立,分別在「敘事」、「戲劇」與「抒情」三大不同性質的創作中達登峰造極之境。
《堂吉訶德》是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文學作品,它不但揭示了歐洲長篇小說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同時也為西方文學史奠定下紮實的基礎。《堂吉訶德》揉合了拉丁古典小說、西班牙民歌、田園小說、流浪漢小說和騎士小說等多種特質,建構出獨特的寫作手法,特別是在故事的鋪陳轉折與人物的刻畫上,別具新意、寓意深長。另外,書中現實與荒誕、魔幻與寫實共存並立的筆法也讓塞萬提斯被尊為後現代小說之祖,對現今已占世界文學一席之地的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作品,頗有推波助瀾之功。時至今日,《堂吉訶德》在全世界已翻譯成七○多種文字,有二千多種版本。一部偉大的經典在經過時間的粹煉後,將閃耀出更動人的光芒。因此,數百年來,我們不斷見證了堂吉訶德的不朽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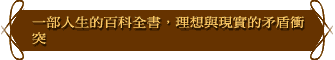
杜斯妥也夫斯基說:「到了地球的盡頭時,如問人們,『你們可明白你們在地球上的生活?該如何作一總結呢?』那時,人們便可以默默將《堂吉訶德》遞過去,說:『這就是我對生活所做的總結……』」
《堂吉訶德》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鉅作,塞萬提斯透過堂吉訶德的三次冒險,帶我們一起遊歷了十六、十七世紀西班牙社會的真實場景,對當時的生活百態、人情風俗,都作了忠實的呈現。書中近七百個、來自不同階層的人物角色,反映出包羅萬象的人性特質與豐富情感,彷如一部人生的百科全書,讓讀者在閱讀時,不自覺產生共鳴之情與情感上之寄託。此外,《堂吉訶德》隱含著一個重要的命題: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塞萬提斯透過堂吉訶德與桑丘,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巧妙地闡述此一觀點。
堂吉訶德和桑丘的關係,是一種有趣詼諧的對立:前者高瘦,後者矮胖;前者為了追求理想而瘋癲荒唐,後者則膽小怕事,事事務實。不過,隨著小說的進展,兩人的性格卻互相影響,各自開拓出不同的視野,如一向言語粗俗的桑丘竟可在人生課題上,說出這樣的道理:「每枚棋子都有自己的功用;下完棋,就都混在一起,裝在一個袋子裏,就像人活了一輩子,埋進墳墓裏一樣。」而滿口騎士道的堂吉訶德到最後竟也悲嘆:「我過去整天讀那些該死的騎士書,讀得神志不清,現在又恢復了理智,心裡明亮得多了。」申言之,這不只是堂吉訶德騎士夢的破滅,同時也說明了理想與現實是一個人一生中必須面臨的最後抉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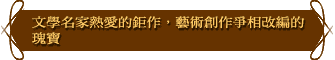
福克納:「我每年讀一遍《堂吉訶德》,就像別人讀《聖經》一般。」
《堂吉訶德》是數百年來無數文學名家所熱愛的經典鉅作,舉凡馬克.吐溫的《湯姆歷險記》、菲爾丁的《堂吉訶德在英國》、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傳》及葛雷安.格林的《堂吉訶德主教》等名作都或多或少曾受到它的影響。塞萬提斯在一六○五年所創作的這部長篇鉅作,至今日在世界各國已翻譯出版達千餘次,是全世界僅次於《聖經》發行量最大的書籍。此外,在眾多文學改編的藝術創作中,《堂吉訶德》可算是其中名列前茅者。光是電影部分,就有近五十部,那就更別說戲劇、音樂劇、芭蕾舞劇等其他形式的創作,諸如百老匯的音樂劇《夢幻騎士》、彼德.葉慈兩千年新拍的電視版、多明哥喜愛的馬斯奈五幕歌劇,以及理查.史特勞斯以幻想風格變奏曲形式所寫成的交響詩……,每一部作品都獲得廣大觀眾的一致好評。一部偉大的文學創作不僅能帶給閱讀者雋永的影響力,引發深沈的思考;激起藝術創作者繽紛多彩的創作靈感,同時也蘊含了流傳千古的永恆價值,而《堂吉訶德》正是最好的範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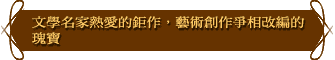
文字是思維的體現,繪畫是想像的延伸,當文字與繪畫完美契合時,閱讀將成為一種無可言喻的感動。
遠流版的《堂吉訶德》是西班牙原文直譯的版本,採用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教授屠孟超教授的譯作。屠孟超教授在中、西文上都有極佳的駕馭力,知名譯作不計其數,包括《人鬼之間》、《佩德羅·巴拉莫》、《藍眼人》、《蜘蛛女之吻》等十餘部。其所譯之《堂吉訶德》完整呈現原著風貌,以口語化、生活化的筆調將書中精彩的俚語、方言詮釋得惟妙惟肖,即使是原文中不易理解的典故,也都能讓讀者一目了然、心領神會,此外還增列八百餘條註釋,協助讀者了解當時語言、社會、文學等背景狀況,深刻感受原著的文學之美。除了塞萬提斯的文字外,更精選了一九○幅法國畫家杜雷的插畫。杜雷以豐富的想像力和細膩的筆觸,描繪出《堂吉訶德》裡壯麗且奇妙的場景,畫中濃淡得宜的線條將景物、人物的立體感和光線明暗都表現得層次分明、令人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