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646年
第一章 台夫特
十六歲的瑪利婭一直不明白,為什麼爸爸決定要離鄉背井,前往「福爾摩沙」那個與荷蘭完全不同的蠻荒世界。
瑪利婭一家人住在台夫特的新禮拜堂旁,有一棟雖然不大但很舒適的房子,三層樓,五個房間,而且靠著運河。他們家有一艘大船、一艘小船,瑪利婭最喜歡和姊妹們划著小船,在台夫特的運河中穿梭。她們的爸爸是牧師亨布魯克,生於鹿特丹,從萊登神學院畢業後派駐到台夫特牧會,在台夫特和安娜成婚,小孩也都是在台夫特出生。他們一家人在台夫特備受尊重,一直過著其樂融融的日子。
爸爸決定去福爾摩沙,是因為聽了他在萊登大學神學院的前輩學長尤羅伯牧師對福爾摩沙的描述。尤羅伯在福爾摩沙前後服務了十四年,一六四三年才離開福爾摩沙回到荷蘭。
尤羅伯回到故鄉台夫特以後,對福爾摩沙人一直念念不忘,於是在這一年春天一個下雨天的下午,來到了亨布魯克的家。
瑪利婭永遠忘不了,她在客廳門後偶然聽到的爸爸和尤羅伯的對話。
「既然他們有獵人頭的惡習,為什麼你那麼喜歡他們?」爸爸問道。瑪利婭正要端出小餅乾招待客人,偶然間聽到「獵人頭」的字眼,不由得屏氣聆聽。
「說起來很矛盾,他們確實有獵頭的習慣,但他們並不是食人族,也不凶暴。」 尤羅伯解釋著福爾摩沙人的生活習俗。「這麼說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其實福爾摩沙人算是善良的民族,他們獵頭只是個不幸的習俗,用來證明狩獵者的勇士氣魄。他們並不愁吃,因為福爾摩沙的整個大草原到處是梅花鹿。福爾摩沙人很聰明,有計畫地捕殺野鹿,絕不過量,人與鹿群維持著很好的平衡。福爾摩沙人太好命了,只有梅花鹿以及各種美麗的鳥類,卻沒有老虎、獅子等凶惡的動物,會傷人的頂多只有一些野豬。聽說高山的地方有一些黑熊,還有體型比較小一點的豹。
「也就是這樣舒適的環境,使得福爾摩沙迄今沒有進入農業社會,因為他們不需要,因為要得到食物太方便了,不必辛苦耕種。在這樣舒適的環境下,福爾摩沙人的男人要證明自己是勇士中的勇士,就去獵野豬。而部落及部落之中總免不了衝突,一衝突就會有械鬥,於是割取對方的人頭成了勇士的象徵。」
話鋒一轉,尤羅伯談起他在福爾摩沙宣教的心得:「所以只要教以基督教義,讓他們有文明觀念,要好好相處,大家相愛,不要互相殺來殺去,不要把獵頭當成勇士象徵,一方面可以救許多人,一方面我們的改革教派會在福爾摩沙找到最好的信徒。
「雖然巴達維亞的土人更多,但大多是穆斯林的異教徒,沒有辦法接受基督。福爾摩沙人不同,他們沒有什麼信仰,一張白紙,而且還算聰明。我和我的前任甘治士牧師為他們創造了一些拉丁拼音文字,教他們用自己的語言唸聖經,倒還有些成績。我在福爾摩沙十多年,有上千福爾摩沙人受洗。在福爾摩沙傳教,會讓你很有成就感。」
尤羅伯說到最後,語氣裡顯然帶著得意。他那天和爸爸談了一整個下午,還留下來吃晚餐。在餐桌上,他取出一張東印度地圖,那是瑪利婭沒有見過的世界角落。本來瑪利婭以為,東方就是出產漂亮絲綢與青花瓷的大明國,現在台夫特就興起一股製造東方風格青花瓷的風潮。她沒想到,東方仍然有存在獵人頭土著的大島嶼,而這個島嶼的名字竟然叫「福爾摩沙」。福爾摩沙是「美麗之島」的意思,這與獵人頭土著多麼不相稱!
這天之後,爸爸又和尤羅伯出去了幾次。媽媽說,他們是到台夫特的東印度公司會所去談。瑪利婭知道東印度公司,他們在台夫特擁有一大排的倉庫。一個月以後,爸爸就向家人宣布,全家要到福爾摩沙。
第二章 瑪利婭
媽媽本來很有些意見的。媽媽對爸爸說,人家尤羅伯是一個人去的,你卻要帶著一家人,何況最小的妹妹克莉絲汀娜還未滿四歲,你應該讓年輕一點的牧師去。
瑪利婭也很難過,因為她正開始喜歡上楊恩.范布來伊森(Jan van Pruyssen)。范布來伊森家和亨布魯克家住得很近,兩家也有些來往。范布來伊森家的二女兒阿格莎與瑪利婭、瑪利婭的姊姊海倫年齡相仿,常常玩在一起。楊恩是阿格莎的小叔叔,雖然是叫叔叔,其實只比阿格莎大了六、七歲,卻一副老成穩重的樣子,在哥哥的樂器店幫忙,也算是個學徒。他說,他將來的志向是有些積蓄之後,到鹿特丹去開一間樂器行。但是開樂器行必須有很大的成本,所以他要更努力。他本來和瑪利婭的一位表姊訂了婚,結果這位表姊突然急病過世了,讓楊恩傷心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也許因為販賣樂器的關係,楊恩本身也吹得一手好木笛。有時在夏天月光灑了一地的晚上,瑪利婭倚在自家的窗戶邊,聽到悠揚的笛聲沿著運河傳來,讓她精神一振。瑪利婭也喜歡音樂,可是大部分的樂器都太大、太貴、太複雜,正好木笛又簡單又便宜,而笛聲可以悠揚、可以婉約。瑪利婭好希望能向楊恩學木笛,但少女的矜持與禮教讓她總是放不開。而自從半年前,楊恩的未婚妻過世之後,運河上傳過來的笛聲由悠揚輕快轉為哀怨憂傷,讓瑪利婭很是不忍,有時會去找楊恩,去安慰他,兩人開始有些私密的來往。一、二個月前,瑪利婭真的跟著楊恩學起木笛來了,兩人以木笛教學為名,定期見面,雙方知道互相喜歡,但都不敢說出來。
瑪利婭熱情奔放,和嚴肅的父親很不一樣,而比較像媽媽安娜。安娜喜歡小動物,喜歡畫畫,也喜歡邀請朋友或鄰居來家裡作客,吃自己做的小餅乾。亨布魯克家教很嚴格,瑪利婭不敢讓父母知道她與楊恩之間的交往,這可是驚世駭俗的,何況她生長在牧師家中,還有個大她一歲的姊姊海倫。
離開台夫特前一個月,瑪利婭終於忍不住哭著告訴父母,她喜歡上了楊恩。夫婦倆對這個早熟、任性的二女兒又是不滿、又是心疼,本要狠狠搬出一番道理的,但因為已決定全家去福爾摩沙,對女兒們也不免有些愧歉,對她們未來婚事有些遠憂。由於夫婦倆對楊恩家父母也都認識,過去已有好印象,就邀請楊恩到家中作客,這讓瑪利婭喜出望外。只不過女兒還未滿十七歲,楊恩的未婚妻也才過世一年,現在談婚事未免太早也太唐突。然而真的一別之後,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聚,大家都有些惶恐。
瑪利婭又笑又哭的,楊恩則保持一貫沉穩斯文樣。亨布魯克與東印度公司的合約是十年,楊恩說他打算用五到七年的時間存錢,然後到福爾摩沙迎娶瑪利婭。跟著哥哥做樂器生意不可能賺很多錢,倒是最近他為人配樂作詞,收入不無小補,他發現自己在這方面算是有些天賦。
楊恩對瑪利婭靦腆地說:「昨天晚上,望著月亮,我寫了一首歌詞送妳,但來不及配上旋律。讓我慢慢來,將來寄到福爾摩沙給妳。」
那天夜裡,瑪利婭遙望著橋頭的風車,想到過去幾個月來兩個人在風車下的歡樂時光,不禁輕輕吟著方才楊恩寫給她的歌詞:
運河裡的溪水 靜靜流
彎彎的月兒 掛天空
永在我腦際的 妳的倩影
那遙遠的福爾摩沙呀……
大教堂的鐘聲 陣陣響
溫煦的太陽 掛天空
永在我心頭的 妳的微笑
那遙遠的福爾摩沙呀……
小橋畔的風車 徐徐轉
閃亮的星星 掛天空
永在我耳際的 妳的笛聲
那遙遠的福爾摩沙呀……
一六四六年耶誕節過後,亨布魯克帶著太太安娜、十七歲的海倫、十六歲的瑪利婭、十歲的漢妮卡和三歲的小女兒克莉絲汀娜,自鹿特丹出發,航向遙遠的福爾摩沙。
第三章 麻豆社
今天是烏瑪大喜的日子,從今天起,她和直加弄就可以互稱「牽手」了。
烏瑪穿起她最漂亮的衣服,頭戴著檳榔花和雞冠花編成的花圈,嘴角含笑,卻又嬌羞不勝地低著頭,右手則緊緊牽著直加弄的左手。梅雍,烏瑪的母親,高興得合不攏嘴,和直加弄的母親佟雁一直有說有笑。烏瑪的生父桑布刀已經過世,現在梅雍和桑布刀的弟弟里加在一起。里加雖然掩不住心中的喜悅,卻保持一貫的威嚴,直挺挺地坐著,有一搭沒一搭地,和直加弄的父親提大羅邊嚼檳榔邊交談。
身為麻豆社最孚眾望的前長老桑布刀的獨生女,又是部落公認的第一美女,烏瑪自然是全社男子的夢中情人;但也因為她是桑布刀的女兒,社裡的男子不免愛在心裡,卻又躑躅不前。
桑布刀在麻豆社裡是個傳奇,但也是半個禁忌。他在十七年前率領麻豆社,一口氣殺掉六十三個荷蘭兵士,那是荷蘭人來到福爾摩沙的第五年。荷蘭人和麻豆社人結怨甚早,早在一六二三年荷蘭人正式到來之前,利邦上尉帶著荷蘭士兵及奴隸來此勘查時就曾發生衝突,雙方均有死傷。而自從荷蘭人來此,本地人變得要繳稅,麻豆人更是不高興。再加上當年的荷蘭長官努易茲年少高傲,被日本武士綁架過,好不容易被釋放後竟然不知悔改,不但對麻豆社人頤指氣使,而且愛好女色,有時要麻豆社女性去陪睡,本地人早已氣他在心。而努易茲竟然在離職前九天派了六十三人的隊伍來麻豆社,號稱是搜捕「漢人海盜」,主要目的其實是要求麻豆社人允許荷蘭人及大明漢人進來墾殖、種甘蔗、種稻、捕鹿、捕魚等。
那時已擔任長老多年的桑布刀認為,荷蘭人也不是第一次來了,但這麼大陣仗前所未見,根本是武力示威。這個看法得到其他十一位長老的支持。於是表面上虛與委蛇,假意協助搜捕逃犯,還拿了兩、三罐酒出來,與荷蘭人一同盡情飲酒。荷蘭軍隊準備離開的時候,麻豆社人假意禮貌地護送他們離開村莊。一行人離開部落,往南走了約半小時之後,來到一處需渡河的地方,麻豆社人依照規定及慣例幫忙扛武器,並揹荷蘭士兵過河。到了河中央,一聲暗號,所有麻豆人側身把荷蘭人翻落水中,而沿著河岸藏匿在樹叢後的麻豆社人也紛紛現身,荷蘭士兵不是被麻豆社人強壓淹死,就是給一刀斬了,除了一名漢人翻譯員和一名奴隸外,沒有活口。這件事震驚了大員的所有荷蘭人。
九天之後,荷蘭長官樸特曼來到大員上任,由於情況不明,遲遲不敢採取報復行動。麻豆社人好生高興,一時在西拉雅族中聲威大盛,桑布刀也因此成了英雄。
可是,六年後冬天的一個晚上,新港社人竟然甘心為荷蘭人的馬前卒,突襲麻豆社。
那一年,烏瑪九歲。她還記得那恐怖的一夜,一群荷蘭兵士騎著馬,突然闖入村落。荷蘭人的槍聲劃破了寧靜的夜空,狗群在馬後狂吠,荷蘭步兵擊鼓跟進,新港人則吆喝著,放火燃燒麻豆人的房屋,麻豆社的房屋幾乎燒光了。本來十一月的晚上已有寒意,火焰反而讓大家覺得炙熱,火花四處飄飛甚是恐怖。烏瑪和族人們躲在海邊的小樹林中,她流著眼淚,卻不敢出聲,只能瑟縮在媽媽身邊,媽媽則抱著弟弟阿僯。每次槍聲一響,大夥兒趕緊把眼睛閉起來。那是烏瑪第一次聽到槍聲,第一次聽到鼓聲,也是第一次看到馬。那些荷蘭人並不高大,在馬上卻顯得好猙獰,來去如風,加上槍枝可以殺人於遠距離外,烏瑪覺得他們不是人,是魔鬼。
麻豆社裡反應最快的勇士衝出去抵抗,但還沒有接近敵人就應聲倒地,讓全村大駭。桑布刀與長老們因此下令不要抵抗,以免做無謂的犧牲。還好敵人並沒有進一步屠殺全村,他們進入村子後只是放火燒屋;有幾位勇士和可惡的新港人力拚,不幸被新港人割了人頭。桑布刀處在隊伍最後掩護族人,但被新港社人所擒。等到麻豆社人集結成小隊逃離村落時,荷蘭人卻制止新港人追殺麻豆人,因此麻豆人才能保存大部分的族人,逃到海邊。
火燒部落後第三天,荷蘭人先回到赤崁。麻豆社長老們出面向新港社人表示希望贖回桑布刀,沒想到新港社人反而砍了桑布刀的頭,把人頭高掛在竹竿上。梅雍哭得昏了過去,烏瑪也大哭,里加和麻豆社人咬緊牙關,誓言要取新港社至少三個人頭來復仇。
麻豆社長老們清點了一下,發現一共有二十六個勇士遭到殺害。里加反而鬆了一口氣,他說,六年前,我們殺了六十三個荷蘭人,聽說那是大員荷蘭軍隊的十分之一,現在他們來了將近五百名荷蘭人,加上一千二百名新港社人,只殺了我們二十六人。麻豆社人突然覺得荷蘭人沒有那麼壞了。麻豆社有好幾千人,如果荷蘭人也放任新港社人殺個十分之一,那麼麻豆社就將鬼哭神嚎了。於是,長老們先拜託宋哥出面代為乞和。宋哥是綽號「烏嘴鬚」的大明國漢人,已經住在麻豆社很久。他長年向荷蘭人付租金,是承包麻豆社的獵鹿執照及鹿皮交易的?商,西拉雅話和荷蘭語都懂,和荷蘭人關係也不錯。
烏瑪記得,接到荷蘭人的議和條件後,麻豆社的頭目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荷蘭人沒有要求再處決任何人,索取的財物也不算多,只希望歸還當年自荷蘭人身上取得的東西,以及奉獻一些豬、牛及檳榔等。他們要麻豆人發誓不再殺害荷蘭人,也不可以干擾漢人;如果其他社的人到大員開會,麻豆社人也要派代表過去;將來如果荷蘭人提出要求,麻豆社人必須協助他們作戰;如果荷蘭代表前來訪問,麻豆社人應該接待。然而荷蘭人提出的一個條件,讓麻豆社的長老們起了爭吵。荷蘭人要麻豆社人「讓渡所有權」給荷蘭,並拿檳榔或椰子的樹苗,送到荷蘭人在大員的城堡為誌。
麻豆人對「所有權」的字眼起了爭執。六年前,桑布刀會設計殺荷蘭人,就是因為荷蘭人常常未經他的允准,便讓漢人經過麻豆社去獵鹿,或去魍港捕烏魚。雖然麻豆人並不吃烏魚,但是桑布刀認為,那些漢人必須經過麻豆社人的允准,而不是經過荷蘭人的允許。同樣的,漢人來捕鹿,必須經過麻豆社人的允許,必須付錢給麻豆社人,可是漢人認為只要向荷蘭人包租就可以了。烏魚還好,鹿群可是麻豆社人的命脈,而且可惡的是,那些漢人常常在不應該捕鹿的季節去捕鹿,設的陷阱又特別厲害,連小鹿也被殺死了。
桑布刀死後繼任長老的里加說,如果依照荷蘭人的條件,把「所有權」讓渡給荷蘭人,應該單指捕魚和捕鹿的權利吧?還是將來種出來的糧食、種出來的檳榔、養出來的豬,都要繳給荷蘭人去分配?烏嘴鬚說,荷蘭人要求的只是「捕魚權」、「捕鹿權」的讓渡,至於住民生產出來的東西,荷蘭人只要求麻豆社每年繳納一定數目的鹿皮、豬、檳榔、椰子等,當做「稅收」。烏嘴鬚對里加說,荷蘭人對他們漢人不但有包租各個項目的?稅,還有「人頭稅」;而荷蘭人認為麻豆社人原本便擁有這塊土地,所以不必繳人頭稅。這是麻豆社人第一次聽到「主權」和「稅」的觀念,覺得非常新奇。
烏嘴鬚又說,新港社、蕭?社、大目降社等都已經答應荷蘭人的條件,如果麻豆社人也答應了,將來麻豆社人到各社都會受到友善的招待。這在麻豆社人聽來是不可思議的事。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部落,聽命於一個「政府」的「法律」,彼此和睦相處,就叫做「秩序」?
烏嘴鬚說:「我們從唐山那邊過來,唐山那邊也是這樣的。」里加問烏嘴鬚:「那麼,你們唐山那邊的政府好不好?為什麼你要過來麻豆社生活,不住在故鄉唐山?為什麼要離開你的故鄉和你的族人?」
烏嘴鬚嘆了一口氣說:「這事情說來話長。首先,這幾年,唐山國內有戰爭,實在不怎麼安定。再說,我們在唐山的土地沒有你們土地這麼肥沃,種起甘蔗長這麼快、這麼甜、這麼茂盛。我們那邊海裡的魚群雖然也多,但你們這裡的烏魚比較多,我們很喜歡吃烏魚的卵,我們叫做烏魚子,是下酒的好菜。我每年冬天在這裡抓一個月的烏魚,運到唐山去賣,可以發一筆小財,讓故鄉的父母妻子兒女有錢可以過個好新年。」至於官員嘛,烏嘴鬚說,唐山和荷蘭的制度各有其好壞。不過他認為,荷蘭的官員算是公平的,而荷蘭傳教士的精神更是讓他很感動。
「荷蘭人來這個島有兩個目的,一是占據這裡的港口,作為貿易的轉運站,收集他們國內喜歡的東西運回去,只要能大賺一筆就好。還好荷蘭人不會把我們當奴隸販賣,雖然我們在這裡很辛苦,有點像奴工,不過是志願的,」烏嘴鬚苦笑了一下,「我聽說在南洋有些地方,島民會被抓到別的地方當奴隸。我自己在大員就看到一些他們抓來的黑奴,來自南洋一個叫班達的島嶼。其實除了荷蘭以外,還有其他國家也會這樣,包括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聽說西班牙人很凶暴,在呂宋動不動就殺死成千上萬的唐山人。」
「荷蘭人除了來做轉口生意外,另外有一些熱心的牧師,來這裡的目的是傳播他們的宗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傳教,但那兩個國家傳的是天主教,荷蘭人的宗教聽說是叫做『改革教派』。」烏嘴鬚又說:「不久以後,這些牧師也會來要求你們信他們的上帝。」
里加表示不願意接受荷蘭人的「主權讓渡」條件,但其他長老大多贊成。里加知道不答應也不行,因為麻豆社人打不過荷蘭人。他也不願意信仰荷蘭人的上帝,他信的是麻豆社祖先們傳下來的阿立祖。於是,里加決定辭去長老之職,以利和議進行。麻豆人先交付了九隻活豬及六枝最大的鏢槍給新港人,請求和平相處。
烏瑪記得宣讀條款時,有一位穿著黑袍的荷蘭人以荷語及西拉雅語宣讀,烏嘴鬚則以漢語宣讀,而且做了詳明的解釋。烏瑪那時好訝異,因為所有荷蘭人都穿軍服,只有這位穿黑袍。烏瑪也驚異於這位穿黑袍的荷蘭人竟然能把西拉雅語說得這麼流利。後來烏瑪才知道他是尤羅伯牧師。「請大家特別注意,第二條將你們的主權讓渡給荷蘭王,以及派駐在大員的福爾摩沙長官。不了解的,等一下我再說明。大家都了解嗎?」麻豆社人稀稀落落地說是。尤羅伯說:「其他村落的人聽到麻豆人所說的了,他們已將自己歸屬於我們。現在我們把他們視為朋友,將以前的衝突忘記。」
儀式中間,麻豆社長老提大羅站上了公廨前的廣場。提大羅自荷蘭軍官手上領到一件紫袍、一支橙旗。荷蘭人說,旗是指揮者的象徵,而橙色是荷蘭的代表色;長袍象徵高位,紫色則象徵高貴。尤羅伯則說,以後提大羅就是麻豆社的「頭人」,大家都要聽「頭人」的話,而頭人也要代表各個社,去大員出席福爾摩沙長官所召開的一年一度地方會議。
第四章 烏瑪
烏瑪的牽手直加弄,正是提大羅的大兒子。
直加弄大約已經二十四歲了。去年秋天一次夜祭之中,直加弄看到烏瑪跳舞,先是送了一枝檳榔花給烏瑪,此後幾乎每個黃昏都到烏瑪屋子的窗邊唱歌。直加弄吹奏鼻笛和口簧琴都很好聽。
麻豆社的習俗沒有家庭制度,而是同性別的年齡相近者聚住一起,所以烏瑪和其他女孩同住一個大房子;烏瑪的弟弟阿僯、直加弄和村裡一部分年輕男性,共十多人,一起住在另一間大竹屋,社裡的人稱之為「集會所」。西拉雅人都是這樣的習俗。
直加弄長得高大黝黑,可以獨自一個人獵殺一隻山豬,烏瑪早就對他印象很好。但是因為荷蘭人的關係,里加不喜歡提大羅,連帶不喜歡直加弄。不過,烏瑪的媽媽梅雍以及和烏瑪住一起的同齡姊妹們都喜歡直加弄,而烏瑪的弟弟阿僯與直加弄更是好友。烏瑪和直加弄兩人情投意合,因此大約在上次月圓的晚上,直加弄曾經偷偷潛入烏瑪的住處過夜。而今天,就是正式提聘的大喜日子了。
直加弄的父親提大羅是荷蘭人任命的頭人,母親佟雁也擁有類似祭司的?姨身分,兩人在部落裡的地位都很高。他的父母為了表示敬重烏瑪的雙親,除了請託一位媒人之外,也親自到烏瑪家提聘,而且準備非常豐盛的聘禮。最重要的檳榔自不用說,還有一隻大豬。禮物更包括五件裙子,其中三件是鹿皮做的;另外有五件衣服、一百個竹製的臂環和手鐲、十枚戒指,其中五枚用金屬做成、五枚用鹿角做成,都做得很精緻好看。其他還包括五條粗麻做的腰帶、十件狗毛衣。讓里加笑不攏嘴的是五件康甘布、兩套漢人衣服,以及一個用稻草和狗毛編製的精製頭冠。讓烏瑪和梅雍最高興的則是五雙粗鹿皮製的長統靴,還可以用靴帶綁住腳。部落裡的人都說,這大概是數十年來她們看到最豐盛的聘禮。
直加弄的雙親給足了面子,梅雍和里加也高興地收下聘禮,一切功德圓滿,意味著從今天開始,烏瑪和直加弄就是眾人眼中的「牽手」了。到了晚上,直加弄可以公然留在烏瑪姊妹們的房子過夜,和烏瑪同眠共枕,可是第二天早上還是必須離去,回到他原來住的集會所。要等兩人年紀更大,有了小孩之後,才能搬出去,在田野中另蓋茅屋,住在一起。
第五章 海澄
陸地已經在望,陳澤愉快地斜倚船舷。海風輕拂,冬陽溫煦,他就快回到月港的家。官方在幾年前已把「月港」改稱海澄,但民間仍習慣稱月港。陳澤覺得八個月來的辛勞與倦意全消,沒有這麼真正歡喜過。
他早已決定,登岸之後,他要盡速回去海澄月港的霞寮故鄉。他真高興來得及回家和妻子過年,好好休息幾個月。雖然他已結婚八年,但實際上能和妻子一起過年,這還只是第三次。
這一年三月,他的船載了近百位要移民呂宋的漳州人,以及滿船的生絲和瓷器,自廈門啟程。他在馬尼拉賣了三分之二貨物給西班牙人,又到渤泥把剩下的三分之一貨品賣給了當地蘇丹,然後載了滿滿的銀子到巴達維亞,向荷蘭人換成當地的香料、玳瑁、珍珠、花布等土產。停靠幾天之後,又到澳門把這些土產賣了一些給葡萄牙人,再搭載一些葡萄牙、日本及大明國乘客,現在正要回到廈門。這個航程經過西班牙、荷蘭、葡萄牙的三個領地,整整航行了近八個月。
想著想著,陳澤真是好生佩服大老闆鄭芝龍。這三個洋人國家在南洋海域中互不相讓,爭來鬥去,鄭芝龍卻在這些洋人領地之間穿梭自如、左右逢源,大賺洋人的錢,真是和氣生財的「生理人」。說是和氣生財,也不盡然。陳澤還記得,荷蘭人在十幾年前想要來硬的,鄭芝龍就絕不低頭也毫不含糊。荷蘭人既然敢放馬過來,鄭芝龍就在金門的料羅灣正面迎敵,把由荷蘭福爾摩沙長官樸特曼親自領軍的艦隊打得抱頭鼠竄。此後,鄭芝龍就把荷蘭人吃得死死的。
荷、葡、西均有政府做後盾,鄭芝龍只憑著一己之力,擁有一千五百艘以上的艦隊,在日本、福爾摩沙到整個南洋之間耀武揚威,也為閩南子弟帶來工作與財富。何況,鄭芝龍還不只做生意賺錢,甚至拜官進爵,是真正像算命仙所說的「財官兼美」。陳澤一直崇拜鄭芝龍,雖然鄭芝龍是泉州人,而泉州人和漳州人過去一直是格格不入的。
鄭芝龍不但會做生意、會做官、有勇氣,而且語言天才更讓陳澤佩服。鄭芝龍的傳奇,在泉州和漳州無人不耳熟能詳。鄭芝龍十八歲時就到澳門打拚,又到呂宋,在那裡差點為西班牙人所殺,他竟然能逃出。然後到三佛齊(今日印尼蘇門答臘的巨港)、到萬丹(爪哇島西部)、到日本平戶,還娶了日本姑娘,鄭芝龍的長公子就是這位日本太太生的。又擔任闖入澎湖的荷蘭艦隊司令雷爾生的顧問兼通譯。後來鄭芝龍到了福爾摩沙,再回到廈門,一方面做朝廷的官,一方面與各國洋人做轉口貿易。對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鄭芝龍都可以直接交談,甚至還有洋名 Nicolas;日本話之流利就更不用說,聽說幾十年前還見過日本現在幕府將軍的世祖德川家康呢,真正太厲害了。陳澤也學他,到了巴達維亞練幾句荷語,到了渤泥就講穆斯林的阿拉伯語,到了澳門則學幾句葡萄牙語,至於馬尼拉的西班牙語,陳澤從小就懂一些,現在更在行了。
船開始駛入一些海島之中,鼓浪嶼、大嶝已在望,廈門也快到了。陳澤這艘船不是普通商船,而是大桅帆船,寬三丈五尺,長十三丈,載重量之大,相當突出,所以能一路遠赴南洋爪哇的萬丹、巴達維亞,或蘇門答臘的舊港。
如果船不往廈門而左轉往九龍江駛去,就是他的家鄉月港。陳澤孩童之時,月港才是大港,廈門尚未發展。只可惜近十多年來,月港已經開始走下坡了。
想當初隆慶、萬曆年間,海禁初解,大明朝廷允許本國國民出海貿易,但嚴查外國商船的進出貿易,所有出洋的商船必須從月港出發,並在月港到廈門的九龍江水道上,接受層層關卡的盤查。朝廷為了方便管理,在月港設立了海澄縣,取「海疆澄清」之意。
隆慶、萬曆年間,正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東來的時期,蓬勃興旺的國際貿易充實了國庫,也帶來福建東南的繁榮;特別是月港,連西班牙銀幣都廣泛流傳。陳澤自小就喜歡在九龍江內游泳,在港口玩時,常接觸到西班牙水手與商人,所以很早就學會簡單的西班牙話,西班牙銀幣更是月港人的最愛。漳州海澄的月港成為唐山最繁榮的港口與城市。
由於海外貿易盛行,福建東南沿海子弟由小農民或小漁民變成大船員或是「生理人」,生活型態大為改變,陳澤就是一例,有不少人甚至移民到南洋去。
第六章 陳澤
一六一七年,大明王朝萬曆四十五年,陳澤在月港附近一個叫霞寮的村莊出生。陳澤是家中長子,父親陳有績也算是霞寮的讀書人家,自然希望身為長子的陳澤也能應考得個功名。陳澤雖然聰明,書也念得不差,偏偏因為年幼時就和洋人接觸,自小希望能到外面世界看看;兼又長得高大壯碩,喜歡舞棒弄棍,也常在九龍江游泳,自嘲為「鴨仔元帥」。幾次鄉試不第之後,陳澤更是一心想出外闖天下,陳有績管他不住,也只能准了。唯一的條件是必須先成婚,才可以出海。於是陳澤依照父命,和鄰里一位郭氏人家的小姐成了親。
鄭芝龍的船隊幾乎一直在擴充,不時招兵買馬。陳澤進入鄭芝龍船隊之後,因為水上功夫好,工作又努力,把吃苦當吃補,很容易就出人頭地。他跑的船愈來愈大,擔任的職位愈來愈高,所到城市也愈來愈遠。
陳澤第一次上船工作,是崇禎十一年或西元一六三八年。那年,陳澤已經二十二歲。陳澤在國外港口跑久了,漸漸習慣陰曆的大明年號和陽曆的西元基督年號並用。陳澤的第一趟,是自鄭芝龍海上跨國企業總部的安海出發,航向大員。這艘戎克船為大員的荷蘭人帶去他們最喜歡的生絲,讓荷蘭人喜出望外。荷蘭人會把這批貨物幾乎百分之百轉口運回歐洲,大賺數倍。
此後三年,陳澤前往大員超過十次。陳澤的船載去生絲、瓷器等,然後載回荷蘭人自南洋帶來的香料,以及福爾摩沙出產的蔗糖、樟腦等。還有最重要的,載人往返福建與福爾摩沙。
自從天啟年間鄭芝龍崛起後,因為他是泉州人,所以他的船大都停泊泉州的安海及廈門為出入口。安海、廈門大見繁榮,屬於漳州的海澄月港就不如以前那麼熱鬧了。這次陳澤的船回國,終於可以回到家鄉,和妻子過年。郭氏溫柔賢淑,小兩口子感情不錯,想到這個,陳澤更是心花怒放。陳澤算是晚婚的,又因為海員生活而聚少離多,兩人迄今尚無所出。五年前父親過世時,就以尚未抱孫為憾。陳澤自忖,已經跑船八年,三十歲了。子曰:「三十而立。」他心中暗中盤算,少則三年,多則五年,積蓄夠了,就自海上生活退下來,也學習自己開行做個「生理人」,並且專心生兒育女。
陳澤自從當了鄭芝龍的屬下,到了許多想都沒想過的外國城市,增長許多見聞,也學了不少外國語言,這些都是福建漳泉父老們所無法想像的。更重要的,鄭芝龍對屬下的海員恩威並施、管理嚴格,但薪俸很不錯。這幾年鄭芝龍的運氣很好,船隻很少出事,真的是飛黃騰達、財源廣進。陳澤短短幾年就甚有積蓄,為幾個弟弟們一一娶親成家,讓鄉里人稱羨不已,有些少年人也就學他投入鄭芝龍的船隊。
本來漳州人和泉州人之間有些相互看不順眼,因為漳州地區的開發時間比泉州晚了數百年,泉州人一向有些看不起漳州人。但是風水本即輪流轉,想想三、四百年前的南宋及元朝時代,泉州港內各國船隻雲集,市內則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食、猶太、錫蘭商賈雜處一地,泉州可說是世界最繁榮的商港,泉州人好風光。不料,明初太祖下令海禁,泉州一蹶不振。等張居正重開海運,卻被漳州月港搶了頭采,因此讓泉州人心中好不平。卻又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先是月港慢慢淤淺,大船進出不易,於是廈門取代了月港。再加上鄭芝龍的個人因素,現在運勢又倒向泉州人這邊了。
但是陳澤心裡覺得這些漳、泉之分完全沒有意義。他雖然年紀輕輕,卻已閱歷多國,見多識廣,看過多樣人種,嘗試過多種文化,更見過各地之土著人民被殖民統治者壓欺的慘狀。他親眼看到西班牙人以呂宋土著為奴,荷蘭人把班達人運送到爪哇為奴。
一六四一年起,鄭芝龍減少到大員的船班,於是陳澤的船隻改為跑呂宋和巴達維亞的機會變多了。西班牙人在呂宋建立一個大城叫馬尼拉,馬尼拉一直是福建移民最喜歡的地方,有漳州人也有泉州人。連西班牙總督都承認,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能有舒服的生活,靠的都是閩南唐山人移民努力做各種市集的工作。
陳澤有次在馬尼拉時,曾聽到當地的唐山人說起一段往事:三十多年前,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不到千人,但已有二、三萬閩南移民,漳州人多於泉州人,偶爾兩族人馬還會爭鬥。一六○三年,大明萬曆皇帝曾派太監及三位京官帶著海澄縣丞、兵丁、隨從,架勢十足,大搖大擺到馬尼拉巡視,把西班牙人嚇得提心吊膽。大明國官員離境後,西班牙人開始防範唐山人,也引起唐山人的不滿,後來演變成閩南移民幾乎完全遭到屠殺的大悲劇,近三萬閩南移民竟然只剩八百人。
而事件過後才一年多,閩南人又大批移民馬尼拉,沒有幾年,馬尼拉的唐山人數目又回到萬人以上。一六三九年,悲劇再起,西班牙人再度對唐山人大開殺戒,殺了好幾千人。在西班牙人的眼中,唐山人就是唐山人,哪有什麼漳、泉之分!
(摘自《福爾摩沙三族記》,遠流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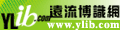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