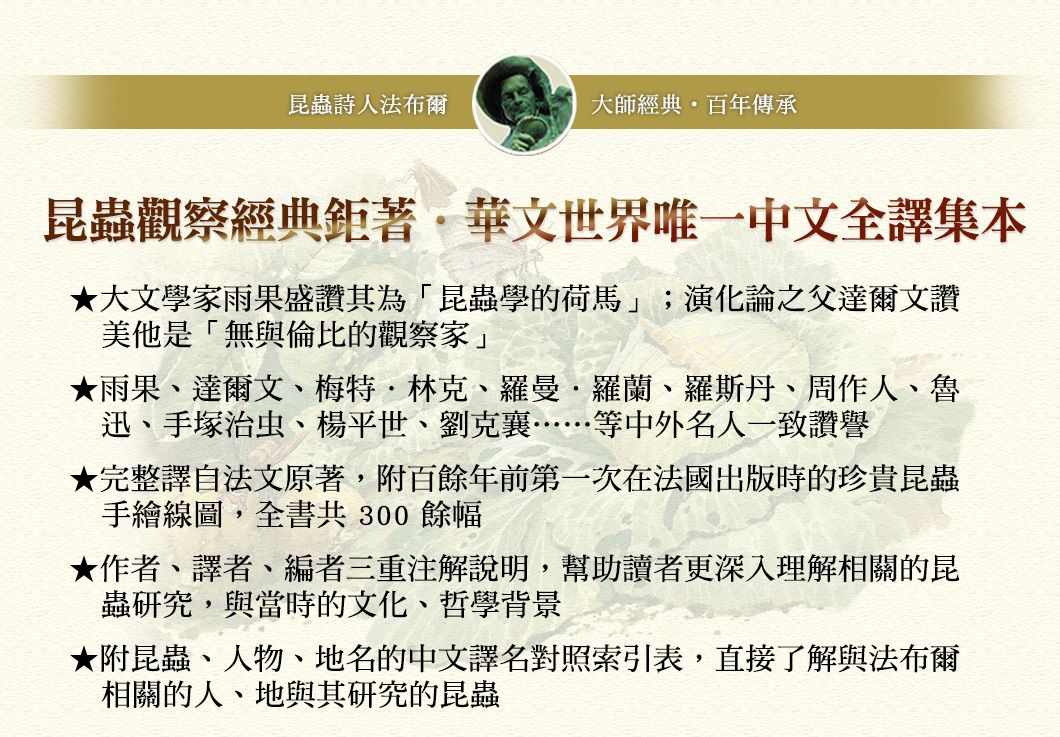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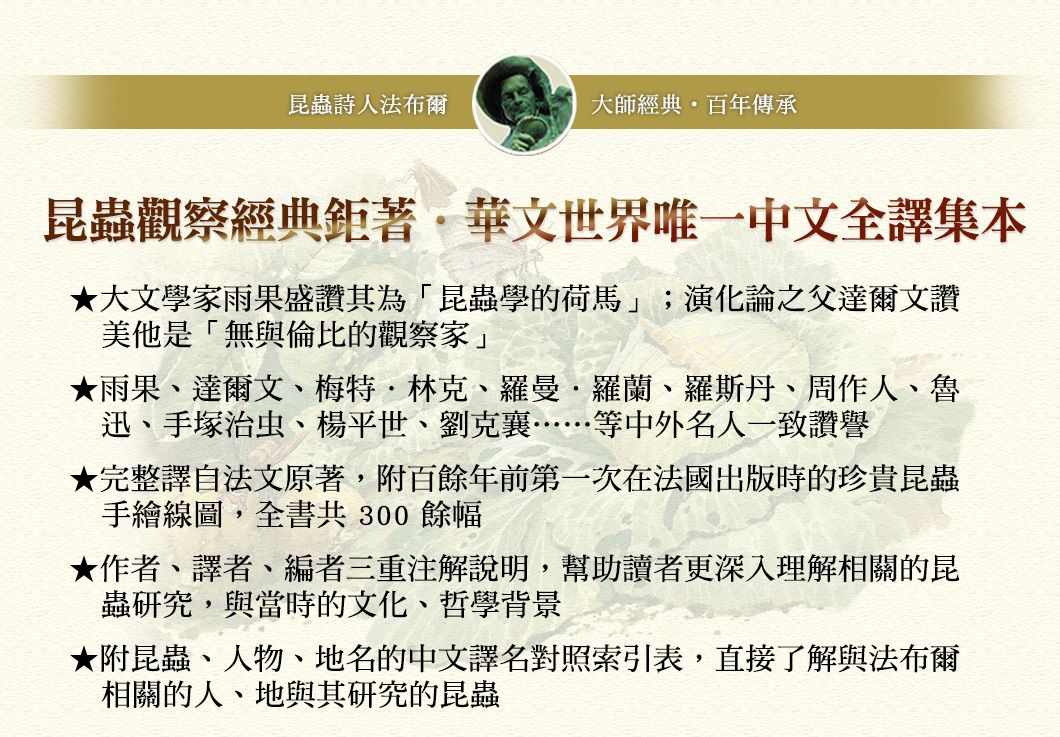

【法布爾昆蟲記全集】(全10冊)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法布爾(Jean-Henri Fabre , 1823-1915)著 / 遠流出版
平裝 / 正25開 / 每冊約368~488頁 / 附精美書衣
定價:3,600元;優惠價 7 折:2,520 元


 蜚聲文壇的昆蟲詩人——法布爾(Jean-Henri Fabre, 1823-1915)
蜚聲文壇的昆蟲詩人——法布爾(Jean-Henri Fabre, 1823-1915)
說實在的,過去我們所接觸的其它版本的《昆蟲記》都只是一個片段,不曾完整過。你好像進入一家精品小鋪,驚喜地看到它所擺設的物品,讓你愛不釋手,但那時還不知,你只是逗留在一個小小樓層的空間。當你走出店家,仰頭一看,才赫然發現,這是一間大型精緻的百貨店。
當完整版的《法布爾昆蟲記全集》出現時,我相信,像我提到的狂熱的「昆蟲王」,以及早熟的十七歲少年,恐怕會增加更多吧!甚至,也會產生像日本博物學者鹿野忠雄、漫畫家手塚治虫那樣,從十一、二歲就矢志,要奉獻一生,成為昆蟲研究者的人。至於,像我這樣自忖不如,半途而廢的昆蟲中年人,若是稍早時遇到的是完整版的《法布爾昆蟲記全集》,說不定那時就不會急著走出小綠山,成為到處遊蕩台灣的旅者了。
《浮生六記》是清朝的作家沈復在四十六歲時回顧一生所寫的一本簡短回憶錄。其中的「兒時記趣」一文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小品,文內記載著他童稚的心靈如何運用細心的觀察與想像,為童年製造許多樂趣。在浮生六記付梓之後約一百年(1909年),八十五歲的詩人與昆蟲學家法布爾,完成了他的昆蟲記的第十冊,也是最後一冊,並印刷問世。
這套耗時卅餘年寫作、多達四百多萬字、以文學手法、日記體裁寫成的鉅作,是法布爾一生觀察昆蟲所寫成的回憶錄,除了紀錄他對昆蟲所進行的觀察與實驗結果外,同時也記載了研究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對學問的辨證,和對人類生活與社會的反省。在昆蟲記中,無論是六隻腳的昆蟲或是八隻腳的蜘蛛,每個對象都耗費法布爾數年到數十年的時間去觀察並實驗,而從中法布爾也獲得無限的理趣,無悔地沉浸其中。昆蟲記的原法文書名《SOUVENIRS ENTOMOLOGIQUES》,直譯為「昆蟲學的回憶錄」,在國內大家較熟悉《昆蟲記》這個譯名。早在1933年,上海商務出版社便出版了本書的首部中文節譯本,書名當時即譯為《昆蟲記》。之後於1968年,台灣商務書店復刻此一版本,在接續的廿多年中成為在臺灣發行的唯一中文節譯版本,目前已絕版多年。1993年國內的東方出版社引進由日本集英社出版,奧本大三郎所摘譯改寫的《昆蟲記》一套八冊,首度為國人有系統地介紹法布爾這套鉅著。這套書在奧本大三郎的改寫下,採對小朋友說故事體的敘述方法,輔以插圖、背景知識和照片說明,十分生動活潑。但是,這一套書卻不是法布爾的原著,而僅是摘譯內容中科學的部分改寫而成。
今天,遠流出版公司的這一套《法布爾昆蟲記全集》十冊,則是引進2001年由大陸花城出版社所出版的最新中文全譯本,再加以逐一修潤、校訂、加註、修繪而成的。這一個版本是目前唯一的中文版全譯本,而且直接譯自法文版原著,不是摘譯,也不是轉譯自日文或英文;書中並有三百餘張法文原著的昆蟲線圖,十分難得。《法布爾昆蟲記全集》第一次讓國人有機會「全覽」法布爾這套鉅作的諸多面相,體驗書中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欣賞優美的用字遣詞,省思深刻的人生態度,並從中更加認識法布爾這位科學家與作者。在法布爾的時代,以分類學為基礎的博物學是主流的生物科學,歐洲的探險家與博物學家在世界各地採集珍禽異獸、奇花異草,將標本帶回博物館進行研究;但是有時這樣的工作會流於相當公式化且表面的研究。新種的描述可能只有兩三行拉丁文的簡單敘述便結束,不會特別在意特殊的構造和其功能。
法布爾對這樣的研究相當不以為然:「你們(博物學家)把昆蟲肢解,而我是研究活生生的昆蟲;你們把昆蟲變成一堆可怕又可憐的東西,而我則使人們喜歡他們……你們研究的是死亡,我研究的是生命。」在今日見分子不見生物的時代,這一段話對於研究生命科學的人來說仍是諍諍建言。
法布爾在當時是少數投入冷僻的行為與生態觀察的非主流學者,科學家雖然十分了解觀察的重要性,但是對於「實驗」的概念還未成熟,甚至認為博物學是不必實驗的科學。法布爾稱得上是將實驗導入田野生物學的先驅者,英國的科學家路柏格(John Lubbock)也是這方面的先驅,但是他的主要影響在於實驗室內的實驗設計。法布爾說:「僅僅靠觀察常常會引人誤入歧途,因為我們遵循自己的思維模式來詮釋觀察所得的數據。為使真相從中現身,就必須進行實驗,只有實驗才能幫助我們探索昆蟲智力這一深奧的問題……通過觀察可以提出問題,通過實驗則可以解決問題,當然問題本身得是可以解決的;即使實驗不能讓我們茅塞頓開,他至少可以從一片混沌的雲霧中投射些許光明。」(見《法布爾昆蟲記全集4》)
這樣的正確認知使得《昆蟲記》中的行為描述變得深刻而有趣,法布爾也不厭其煩地在書中交代他的思路和實驗,讓讀者可以融入情景去體驗實驗與觀察結果所呈現的意義。而法布爾也不會輕易下任何結論,除非在三番兩次的實驗或觀察都呈現確切的結果,而且有合理的解釋時他才會說「是」或「不是」。比如他在村里用大砲發出巨大的爆炸聲響,但是發現樹上的鳴蟬依舊故我鳴個不停,他沒有據此做出蟬是聾子的結論,只保留地說他們的聽覺很鈍(見《法布爾昆蟲記全集5》)。類似的例子在整套《昆蟲記》中比比皆是,可以看到法布爾對科學所抱持的嚴謹態度。
在整部《昆蟲記》中,法布爾著力最深的是有關昆蟲的本能部分,這一部份的觀察包含了許多寄生蜂類、蠅類和甲蟲的觀察與實驗。這些深入的研究推翻了過去權威所言這是既得習慣的錯誤觀念,了解昆蟲的本能是無意識地為了某個目的和意圖而行動,並開創「結構先於功能」這樣一個新的觀念(見《法布爾昆蟲記全集4》)。法布爾也首度發現了昆蟲對於某些的環境次機會有特別的反應,稱為趨性(taxis),比如某些昆蟲夜裡飛向光源的趨光性、喜歡沿著角落行走活動的趨觸性等等。而在研究芫青的過程中,他也發現了有別於過去知道的各種變態型式,在幼蟲期間多了一個特殊的擬蛹階段,法布爾將這樣的變態型式稱為「過變態」(hypermetamorphosis),這是不喜歡使用學術象牙塔裡那種艱深用語的法布爾,唯一發明的一個昆蟲學專有名詞。(見《法布爾昆蟲記全集2》)
雖然法布爾的觀察與實驗相當仔細而有趣,但是《昆蟲記》的文學寫作手法有時的確帶來一些問題,尤其是一些擬人化的想法與寫法,可能會造成一些誤導。還有許多部分已經在後人的研究下呈現出較清楚的面貌,甚至與法布爾的觀點不相符合。比如法布爾認為蟬的聽覺很鈍,甚至可能沒有聽覺,因此蟬鳴或其他動物鳴叫只是表現享受生活樂趣的手段罷了。這樣的陳述以科學角度來說是完全不恰當的。因此希望讀者沉浸在本書之餘,也記得「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名言,時時抱持懷疑的態度,旁徵博引其他書籍或科學報告的內容相互佐證比較,甚至以本地的昆蟲來重複進行法布爾的實驗,看看是否同樣適用或發現新的「事實」,這樣法布爾的《昆蟲記》才真正達到了啟發與教育的目的,而不只是一堆現成的知識而已。《昆蟲記》並不是單純的科學紀錄,它在文學與科普同樣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整部書中,法布爾不時引用希臘神話、寓言故事,或是家鄉普羅旺斯地區的鄉間故事與民俗,不使內容成為曲高和寡的科學紀錄,而是和「人」密切相關的整體。這樣的特質在這些年來越來越希罕,學習人文或是科學的學子往往只沉浸在自己的領域,未能跨出學門去豐富自己的知識,或是實地去了解這塊孕育我們的土地的點滴。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如果《昆蟲記》能獲得您的共鳴,或許能激發您想去了解這片土地自然與人文風采的慾望。
法國著名的劇作家羅斯丹說法布爾「像哲學家一般地思,像美術家一般地看,像文學家一般地寫」;大文學家雨果則稱他是「昆蟲學的荷馬」;演化論之父達爾文讚美他是「無與倫比的觀察家」。但是在十八世紀末的當時,法布爾這樣的寫作手法並不受到一般法國科學家們的認同,認為太過通俗輕鬆,不像當時科學文章艱深精確的寫作結構。然而法布爾堅持自己的理念,並在書中寫道:「高牆不能使人熱愛科學。將來會有越來越多人致力打破這堵高牆,而他們所用的工具,就是我今天用的、而為你們(科學家)所鄙夷不屑的文學。」
以今日科學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陳述或許有些情緒化的因素摻雜其中,但是他的理念已成為科普的典範,而《昆蟲記》的文學地位也已為普世所公認,甚至進入諾貝爾文學獎入圍的候補名單。《昆蟲記》裡面的用詞遣字是值得細細欣賞品味的,雖然中譯本或許沒能那樣真實反應出法文原版的文學性,但是讀者必定能發現他絕非鋪陳直敘的新聞式文章。尤其在文章中對人生的體悟、對科學的感想、對委屈的抒懷,常常流露出法布爾作為一位詩人的本性。(本文為節錄)











這就是我所想要的:一塊地。哦!一塊不要太大,但四周有圍牆,不會有馬路上各種麻煩的土地;一塊日曬熱烤,荒蕪不毛,被人拋棄但卻是矢車菊和膜翅目昆蟲鍾愛的土地。在那裡,我可以不必擔心過路人的打擾,與砂泥蜂和飛蝗泥蜂交談,這種艱難的對話,就靠實驗表達出來;在那裡,無需耗費時間遠行,無需迫不及待的奔走,我可以編製我的進攻計畫,設置我的埋住陷阱,每天時時刻刻觀察所得到的結果。一塊地,是的,這就是我的願望,我的夢想,是我一直苦苦追求的夢想,但將來能否實現卻沒有明確的把握。
所以,一個人整天都在為每日的麵包一籌莫展而操心時,要在曠野裡給自己準備一個實驗室是不容易的。我以不曲不撓的勇氣跟窮困潦倒的生活搏鬥了四十年,結果這朝思暮想的實驗室終於得到了。這是我孜孜不倦、頑強奮鬥的結果,我不想去說它了。它來到了,但伴隨著它而來的,也許是必須要有一點空閒的時間,這是更重要的條件。我說也許,是因為我的腳上總是拖著苦行犯的鎖鏈。願望是實現了,只是遲了些啊,我美麗的昆蟲!我很害怕有了桃子的時候,我的牙齒卻啃不動了。是的,只是遲了些,原先那開闊的天際,如今已成了十分低垂、令人窒息,而且日益縮小的穹廬。對於往事,除了我已經失去的以外,我一無所,我什麼也不後悔,甚至不後悔那二十年的光陰。對一切我也不抱希震,已經到這個地步了,往事歷歷,使我精疲力竭。我思忖:究竟值得不值得這樣生活下去。
四周一片廢墟,中間一堵斷牆聳立,石灰和沙使它巍然不動,這屹立著的斷牆就是我對科學真理的熱愛。哦!我靈巧的膜翅目昆蟲啊!這種熱愛是不是足以讓我名正言順地對你們的故事再添上幾頁呢?我會不會力不從心呢?為什麼我自己也把你們拋棄了這麼長的時間呢?一些朋友為此責備我。啊!告訴他們,告訴那些既是你們的也是我的朋友們。告訴他們:並不是由於我的遺忘、我的懶散、我的拋棄,我想念你們,我深信節腹泥蜂的窩還會告訴我們動人的秘密,飛蝗泥蜂的捕獵還會給我們帶來驚奇的故事。但是我缺少時間,我在跟不幸的命運搏鬥中,孤立無援,被人遺棄,在高談闊論之前,必須能夠活下去。請您告訴他們吧,他們會原諒我的。
還有人指責我使用的語言不莊嚴,乾脆直說吧,就是沒有乾巴巴的學究氣息。他們害怕讀起來不令人疲倦的作品,認為它就是沒有說出真理。照他們這種說法,只有晦澀難懂,才真的是思想深刻。你們這些帶著螫針的和盔甲上長著鞘翅的,不管有多少,都到這裡來為我辯護,替我說話吧!你們說說我跟你們是多麼親密無間,我多麼耐心地觀察你們,多麼認真地記錄你們的行為。你們的證詞會異口同聲地說:是的。證明我的作品沒有充滿言之無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準確地描述觀察到的事實,一點也不少。誰願意詢問你們就直接去問好了,他們也會得到同樣的答覆的。
另外,我親愛的昆蟲們,如果因為對你們的描述不夠令人討厭,所以說服不了這些正直的人,那麼就由我來對他們說:你們是把昆蟲開膛破肚,而我是在牠們活蹦亂跳的情況下進行研究;你們把昆蟲變成一堆既恐怖又可憐的東西,而我則使得人們喜歡牠們;你們在酷刑室和碎屍場裡工作,但我是在蔚藍的天空下,在鳴蟬的歌聲中觀察;你們用試劑測試蜂房和原生質,而我卻是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現;你們探究死亡,而我卻是探究生命。我為平麼不能進一步說明我的想法,因為野豬攪渾了清泉。博物學是青年人極好的學業,可是由於越分越細。
彼此隔絕,如今已成了令人嫌惡的東西。然而,如果說我是為了那些企圖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楚「本能」這個熱門問題的學者、哲學家們而寫,其實我更是為年輕人而寫,我希望使他們熱愛這門被你們弄得令人憎惡的博物學。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極力保持翔實的同時,不採用你們那種科學性的文字,因為這種文字似乎是從休倫人的語言中借用來的。這種情況,唉!真是太常見了。
不過,這並不是現在要做的事。我要談的是在我的計畫中朝思暮想的那塊地,我要將它變成活的動物學實驗室。這塊地,我終於在一個荒僻的小村莊裡得到了。這是一個荒石園,當地的語言中,「荒石園」這個詞指的是一塊荒蕪不毛、亂石遍布、百里香恣生的荒地。這種地貧瘠到使辛勤地犁耙也無法改善。當春天偶爾下又,長出一點草時,綿羊會來到這裡。不過,我的荒石園由於在無數亂石中還有點紅土,所以開始長出一些作物。據說從前那裡有些葡萄。的確,為了種幾棵樹而進行的挖掘中,會從各處挖出一些寶貴的根莖,由於時間久了,部皆已經成了炭。於是,我用唯一能夠掘開這種土地的農具──長柄三齒耙來挖。可是實在太遺憾了,原先的植物已經沒有了。不再有百里香,不再有薰衣草,不有簇簇胭脂蟲櫟,這種矮矮的胭脂蟲櫟會形成小樹林,人只要稍微抬腿一跨就可以走過去。這些植物,尤其是前兩種,由於能夠提供膜翅目昆蟲所要採集的東西,可能對我有用,我不得不它們再栽到用長柄三齒耙掘開的地上。
(中略)這裡的昆蟲的確是既多又齊全,而且我看到的還非常不完整呢!如果我能夠讓牠們說話,那麼跟牠們的談話一定會使我孤寂的生活得到許多樂趣。這些昆蟲,有的是我的舊交,有的是新識,牠們全都在這裡,彼此緊靠著,在捕獵、採蜜、築窩。另外,如果需要改變一下觀察地點,走幾百步就是山,山上有野草莓叢、岩薔薇叢、歐石楠樹叢。有泥蜂所珍愛的沙層,有各種膜翅目昆蟲喜觀開採的泥灰岩邊坡。我預見了這些寶貴的財富,這就是我為什麼逃離城市到鄉村,來到塞西尼翁,為我的蘿蔔鋤草,為我的萵苣澆水的原因了。
人們在大洋洲和地中海海邊花很多錢建造實驗室,用來解剖對我們意義不大的海洋小動物。人們大量使用顯微鏡、精密的解剖器、捕獵設備、小船、捕魚人員、水族缸,以便知道某種環節動物的卵黃如何分裂,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有什麼意義。可是,人們卻瞧不起地上的小昆蟲,這些小昆蟲跟我們息息相關,向普通生理學提供無價之寶的資料;有的損壞我們的莊稼,破壞了公眾的利益。什麼時候會有一個不是研究泡在三六燒酒裡的死昆蟲,而是研究活昆蟲,一個以研究這些小昆蟲的本能、習性、生活方式、工作和繁衍為目的,而我們的農業和哲學應當對此加以考慮的昆蟲學實驗室呢?徹底了解蹂躪我們的葡萄的昆蟲歷史,可能比知道一種蔓足綱的動物某一根神經末梢結尾是什麼樣子更加重要。以實驗來確定智慧與本能的分界,經由比較動物界的各種事實來揭示:人的理性是不是一種可以改變的特性。這一切應該比一個甲殼動物觸鬚的數目重要得多。為了解決這些巨大的問題,必須有大批工作者,可是我們現在卻連一個也沒有。人們想到的只是軟體動物、植物性無脊動物。人們投入大量的拖網來探索海底,但卻對腳下的土地仍然不了解。我在等待著人們改變方式,但在這之前,我開闢了荒石園來研究活生生的昆蟲,而這個實驗室卻無須從納稅人的錢包中掏一分錢。(摘自《法布爾昆蟲記2:樹莓樁中的居民》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