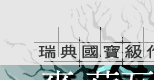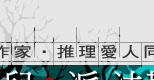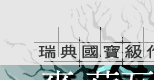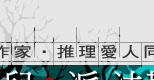|
推理小說誕生於十九世紀中葉興盛於兩個世紀的交替。由於形式獨特(一個類數學解謎的結構)引發了不同背景的作者參與在文學創作史上是個有趣的例子。
醫生加入推理小說的創作帶來藥物與死因的知識;律師、法官加入創作指出法律的漏洞與矛盾;會計師、銀行家加入創作帶來經犯罪的洞察;歷史家加入創作呈現考古與偵探的給合;而當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加入創作時他帶來…?
他(們)帶來十本推理小說的傑作。
我指的是瑞典共產黨員瑪姬‧史菊華(Maj Sjowall)和她的愛人同志皮‧華盧(Per Wahloo)。瑪姬同時是一位知名的詩人皮則是一位受尊敬的新聞工作者以報導文學見重於世。這兩位左翼文學家發現推理小說最足以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病態乃相勉從事自一九六七年間聯手創作了十部推理小說;直至皮‧華盧辭世兩人合創的獨特「馬丁‧貝克探案」就成了絕響。(馬丁‧貝克是瑞典國家警察署的探長也是這一系列小說的主角。)
史‧華二氏的小說獨特之處是什麼?套句英國推理小說家兼推理小說評論家基亭( H.R.F Keating
)的話: 「人生盡在其中。 」( all human life is there )。「人生盡在其中」本來應該用來禮讚莎士比亞或曹雪芹如今卻用來稱許一系列的推理小說可見在評論者心中之地位。
但「人生盡在其中」也反過來說明了大部份推理小說是「人生不在其中」的。推理小說的傳統是解謎而非反映人生;有推理小說家甚至把「寫實」懸為禁忌(如
S.S.Van Done )認為有損推理小說的「一致性」。大部分之正統推理小說(即日本人說的「本格派」)基本上是一場智力遊戲沒有真實社會只有佈景;沒有真實人物只有戲偶--史、華二氏突破了這個限制卻仍寫出相當正統的智力推演小說來的確是個異數。
警察辦案小說
史‧華二氏的推理小說應該歸為正統推理小說中「警察辦案小說」( Police -Procedural
novel 的一支)。小說中的偵探主角不是私家偵探而是國家治安機器的一環:警察。既然是警察就有一定的警察程序得遵守(別忘了他們是執法人員他們的局限也正是「法」);一切智力推演與解謎行動都得依此規律。現實生活中警察辦案程序是存在的這也就有機會使推理小說具備現實生活的合理性寫實態度與推理小說也在這裏有了交會的機會--這顯然是史、華二氏選擇警察辦案小說的原因。
馬丁‧貝克是史、華二氏創造的神探他是瑞典國家警察署的探長(不過在各部小說中他的職務常有升降起伏)在斯德哥爾摩這個現代都會中扮演打擊重案犯罪的角色。他與其他神探一樣心思細密辦案執著對線索有直覺式的敏感;但他與其他神探不同他疲倦失眠胃酸過多婚姻家庭處於瓦解邊緣。小說場景與推理小說的簡單佈景不同,它有高失業率、高自殺率的社會問題問案時會討論到政治、宗教社會複雜性交織在故事的舞台上。
《羅絲安娜》是史菊華與華盧合作的第一部小說但上述的特質已經顯露無疑後來當然繼續出現在其他九部小說之中。做為一個警察辦案故事《羅絲安娜》是很準確也很標準的;小說一開始在運河中發現全裸的無名女屍揭示了謎題困難的是警方不僅不知道兇手連被害人是誰也毫無頭緒附近根本無人失蹤--警察辦展開一定的調查程序不靠靈感才情而是苦功與耐性;神探也不提供天才洞見他只是主持這項繁瑣重複工作的領導者。
從大量的發函中有一個來自美國鄉村的回應有了線索他們查出死者身分她是個觀光客。一個觀光客獨自到了陌生國度結果被謀殺了她在觀光地並無任何人際網路這樣的案件如何查起?--我不能破壞讀者的閱讀樂趣我只能說史、華二氏提供的是一個很具代表性的警察作業步步為營逼向案情核心清理出對象最後繩之以法。
現代都巿危險
不要忘了史、華二氏並不是要提供我們一個娛樂(至少他們原意不是)毋寧說他們想提供一個社會教訓供我們(在娛樂之餘)反省。在《羅絲安娜》裏這個教訓是什麼呢?
這個教訓說明了現代都巿的潛在危險。在現代的工業都巿裏人與人關係不親人人都流離失所傳統社會那種每個人都識每個人的防衛系統消失了這個時侯一種危險正等著我……
你知道你隔壁那位衣冠楚楚、準時上下班的中年男子是個變態殺人狂嗎?我們不會知道因為我們不親近。我們經常要與陌生人在不同場合接觸在旅行團裏、在舞廳、在工作拜訪時我們會與某些人暫時有接觸的關係可是你知道他正上下打量著你對你心懷不軌嗎?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們才見面。
現代社會的人際關係的寫照如此這是一種真相;社會裏也就多出一種沒有頭緒的案件因為那些人際關係短暫而無痕跡並沒有穩定的線索可供你循路探尋--也就是說案件的特性反映了社會的型態。銳利的文學如史、華二氏他們感受到這個危險更把它化為引人入勝的小說。
小說出版的二十年後一位日本年輕女和羅絲安娜一樣自助旅行來到台灣台南路上她將邂逅一些看似熱心善良的限生人有些人的確是但有人卻不是--她後來將慘遭不測屍骨難尋而案子也膠著艱進。其情節與羅絲安娜的遭遇何其相似好的小說具有「預言性」我們在這裏又看到一例。
(本文摘自【謀殺專門店】同一作品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