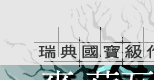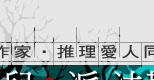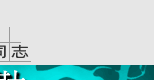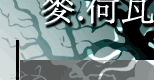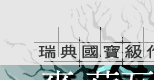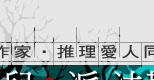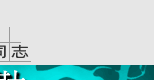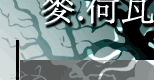| 兇手躲在幕簾後面,等著適當時機狙殺他的獵物:一個在醫院病房等著復原的前警察探長。兇手突然往前一躍,以血腥而令人驚恐的效率,拿刺刀捅他的被害者。不久,他爬上附近某建築物的屋頂,以極度的精確,開始以火力強大的來福槍射殺了更多的警察。
這些是柏˙魏德柏(Bo Widerberg)執導的電影「屋頂上的男人」中的場景,根據荷瓦兒和法勒作品《壞胚子》改編而成。這部電影其他部分非常忠於原著,遺憾的是書名做了更動,因為換了書名後,電影就失去了作品中原有的反諷意味。當然,一針見血的諷刺還是存在,因為這個殺害警察的人本身也曾是個警察;可是更大的諷刺是:原本書名所說的壞胚子並不是指兇手,也就是屋頂上的男人,而是指曾經當過警察探長的那個被害者,因為隨著小說推展,我們慢慢知道,這個被害者是個以無情和粗魯對待被捕嫌犯的人,而後來的調查過程更揭露,兇手無辜的妻子之所以喪生,就是拜這個被害者之賜。因此,最後我們發現:兇手本身是個受害者,諷刺的是,被他殺害的人才是個殺人兇手。
這個故事帶給我們一個惱人的疑問:警察是保護社會不受罪犯侵襲的人,還是讓社會中的無辜者出於報復而犯下罪行的挑撥者?這個問題讓我們對社會中的警察有種矛盾心理,而這也是派˙法勒和麥˙荷瓦兒小說作品的核心所在。
* * *
一九七五年,隨著《恐怖份子》出版而同一年法勒過世,近年來現代小說寫作中最耐人尋味的實驗之一就此告終。根據出版商所提供的簡傳,當過新聞記者的荷瓦兒和法勒在一九六五年決定合寫一系列犯罪小說,以一個名叫馬丁‧貝克的警探為中心角色,隨著他這個打擊犯罪者的腳步,帶領讀者走過瑞典近代十年的歷史。
他們說,這一系列小說是追蹤「一個人的個性隨著歲月演變的過程;這段歲月中大環境和氛圍改變了,政治、經濟、犯罪率也起了變化。」派.法勒曾在一九六六年寫的一篇文章中陳述他和麥.荷瓦兒於一年前開始創作的馬丁.貝克系列的基本原則。這一系列只由十本小說組成。兩人之所以選擇以犯罪小說的形式呈現,乃因它和人民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聯:一個社會若不是根據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政策來執行法律和維持秩序,根本不會有違法者甚至執法者的存在。夫婦倆共同創作,經過長時令間的研究並寫下詳細的摘要後,分頭進行不同的篇章。皆為共產黨的兩人坦承這一系列的主旨是「利用犯罪小說作為替意識型態貧瘠、道德上值得爭議的所謂布爾喬亞式福利制度剖腹的手術刀」。前三部小說中其中兩部幾乎完全和政治無關,後來的幾部將卸下面具直言不諱。
因此,《羅絲安娜》,《蒸發》和《陽台上的男子》都是直截了當的刑事偵查式(警方辦案式)小說:一組工作勤奮的員警偵破謀殺案的過程,其中兩宗甚至是變態案件,理智成了重點。與大多數同類型的小說相較之下,這幾部小說的水準較高,心理層次上更複雜,同時更大為寫實,不過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娛樂效果。
派.法勒夫婦在瑞典警力於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歸屬中央管轄後第八天開始創作《羅絲安娜》。中央接管之後,逐漸以武器、器械及準正規軍組織來取代情理的做法,以及甫獲認命的政治新領袖們群龍無首,這些是這一系列從頭到尾大加撻伐的主要對象。接下來的兩部小說:《大笑的警察》及《失蹤的消防車》開始比較清楚的呈現作者的意圖。在《大笑的警察》中,殺害多人的兇手行兇動機是他想保有其社會地位;而在《失蹤的消防車》中,貝克小組遭逢職業罪犯,專業犯罪在當時的瑞典犯罪小說及瑞典的實際社會上都屬罕見現象。假如在這一系列初期小說中出現的兇手變態,那麼這兩部小說中的兇手便屬超級理性。他們選擇了犯罪作為在瑞典社會中生活的一種方式。
後來的幾部小說經常將犯罪處理成替天行道。《薩伏大飯店》中的商業鉅子及《壞胚子》中的警司都是謀殺案的被害者,但無疑的,他們才是比扣上板機的可憐兇手更受到社會保護的真罪犯。《上鎖的房間》有一個相當精采的約翰.狄克森.卡爾式架構,而且更為狂放,不過書中也沉痛的指出諸如銀行搶劫之類的涉及金錢的罪案在執政當局的眼中遠比殺人案嚴重。《弒警犯》猛烈抨擊新聞媒體報導新聞偏頗,並將貝克小組內老前輩們的專業常識與受馬丁‧貝克的上級偏愛的準正規軍打壓驚慌、孤單又年輕的的違法者的方式做一對比。《恐怖份子》是手術刀劃開福利制度後得出的暨痛苦又合理的結論,這個制度虛有其名,因此,即使對不關心政治的貝克而言,謀殺應對這項制度缺失負責的總理似乎很合理,或許全球大多數的讀者也持相同意見。
和大多數的刑事偵查式小說不同的是,馬丁‧貝克讓主角們隨著年齡增長顯得更形重要,同時更與眾不同,允許他們智慧增長,發展並改變觀點。萊納.柯柏日後有所驛動,因為他溫暖、思路清晰及多情的個性已對社會或其小組無用處。這是作者的神來之筆之一,同時也是個明證,證明作者有能力說服全球的讀者相信,當資本主義國家內一個奉行社會主義的警探有志難伸時,會造成莫斯科與紐約、伯明罕與貝爾格勒當局懊悔不已。馬丁‧貝克一直堅守崗位,但自從在《羅絲安娜》中出現之後的多年來,他也有些變化。在《壞胚子》中,他的事業險些因為他試圖替全組人員擔罪而畫下據點,而在《上鎖的房間》中,他沉緩的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與工作。當他在《恐怖份子》中與我們分離時,他頭上方有一張毛主席的海報。那張海報並非他張貼上去的,但他讓它一直停留在那兒。
法勒和荷瓦兒對這類型小說的主要貢獻是,他們示範了如何運用受歡迎的形式來散佈一種新式、複雜甚至不受眾人歡迎的內容。兩人受到一些政治觀點混亂的美國評論家的誤解,這些評論家聲稱這一系列小說嚴批瑞典社會主義社會。也有人說他們是單純的共黨宣傳人員。這兩種極端的看法都是錯解。在以社會主義者觀點來創作一套精心設計並執行完美卓越的刑事偵查式小說系列的同時,法勒夫婦成功的做了重大的文學嘗試,擴大了偵探小說的範疇,並利用它來討論並評論一個範圍更廣、同時在多方面更是罪惡重重的真實世界。
這些小說每一本以瑞典文出版後,一年半內都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上市,普遍受到好評外,兩位作者的書迷也日增一日。
這些小說不僅比美國每年發行的那些品質普通、一推出就被狼吞虎嚥的警察辦案小說好得多,而且更為有趣、刺激;而其最出眾之處,更在於(一如兩位作者一開始就計畫的)記錄了瑞典社會在十年之間的變化,或是更準確地說,記錄了某些成員對這個社會的看法的改變。藉由這些小說,我們看到作者對這個變動中的國家持久而嚴厲的檢視,雖然這樣的檢視並沒有很多確鑿的社會統計數字作為支持。基本上,作者的焦點集中在瑞典的警政上,所以整套小說構組成了一個對社會中警察的心態轉變的紀錄,而這種心態的轉變主要是藉由荷瓦兒和法勒創造出來的幾個警察角色反映出來,這幾個警察就是這個非常寫實的小說世界的中心。
荷瓦兒和法勒認為他們的社會和警察的角色日益向下沉淪,不管我們多麼同意或不同意,有一點是確定的:那是他們的觀點,而且他們將它無情地揭露給我們看到。但不僅如此,他們也給了我們其他的東西:品質。他們的品質不只表現在簡潔、明快、一針見血的寫作風格上,也不只是在那些刺激萬分而且非常好笑的故事情節中,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荷瓦兒和法勒是極為高明的諷刺家,是書寫系列喜劇推理的高手。而他們高品質的寫作能力最能顯現在角色的創造上,這些角色每一部小說都重複出現,確實令人印象鮮活。有的只是幾筆速寫,例如永遠紅著鼻頭、個性陰鬱的埃拿‧隆恩;過目不忘的米蘭德;好戰好鬥、每部小說裏至少踢倒一道門、同時也很樂於踢爛警政體系的剛瓦德‧拉森。小說中也有較為細膩的角色,例如敏銳而堅持理念的萊納‧柯柏,他在這套小說世界裡是良知的聲音,同時也是智慧的聲音。最後就是馬丁‧貝克了。
就像那位法國神探一樣,馬丁‧貝克也是犯罪文學中的要角。他深知警察工作的重要,在他內心的召喚下,他以高效率也很人性的方法辦案。但身為社會中的警察,馬丁‧貝克也越來越矛盾,因為警察在追捕罪犯的過程中很可能會挑起暴力。他是個富有同情心、敏感的角色,他週遭的世界在變,他自己也在變化。在系列小說的中間幾本,他終於和妻子分開,讓自己從一個令人窒息的婚姻中釋放,體驗到個人的成長。在最後幾本小說中,我們很高興的看到,他邂逅也愛上了本身就混合著自然和自由特質的梨雅˙尼爾森,這是馬丁˙貝克尋覓已久的心靈伴侶。
* * *
不管我們多麼想反駁這兩位小說家有時候可說是先入為主的社會結論,我們還是必須承認他們獨特的成就。這系列小說包含了社會的變遷,因此作者可說是將偵探小說提高到了一種高層次的水平。小說裡有變動的社會,也有在變動下工作、因此受到影響同時也難免影響了社會的人,荷瓦兒和法勒結合了兩者,將這種寫作風格帶入了所謂的全套作品中,而這種文體勢必有它持久的藝術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