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之歌
Song of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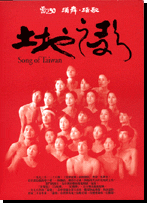 1978年,雲門5歲的時候,「薪傳誕生了!」這是一支會殺人的舞蹈!舞者們說,「跳到最後,我必須心裡喊著,幹!幹!幹!才有力氣繼續跳下去。」 1978年,雲門5歲的時候,「薪傳誕生了!」這是一支會殺人的舞蹈!舞者們說,「跳到最後,我必須心裡喊著,幹!幹!幹!才有力氣繼續跳下去。」
那一年,颱風天,舞者們直奔屏東佳洛水,讓大海的驚濤巨浪撲打在他們身上;因為300年前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渡過黑水溝的!接著舞者們在新店溪畔從搬石頭開始,實地的用身體體會祖先們移民拓荒的艱辛與力氣。他們知道,他們也在台灣的舞蹈界拓荒,所以他們不僅要有先民的身體,他們更要有先民的精神與勇氣。
12月16日,「薪傳」在嘉義體育館首演,當天新聞傳出來─中美斷交。舞台上,舞者們奮力的撕開自己的身體,汗水、淚水不斷的淌湧下來;舞台下,觀眾更是哭紅了眼睛、拍紅了雙手。最後台上、台下交織成一片。舞蹈結束了,戲卻沒有散去,觀眾主動的參與進來,幫忙拆台、搬東西。真實的人生反而更熱烈的上演著,大概全世界也很難再有這樣動人的劇場了。
2002年,林懷民在八里的排練場嘶吼著,「跳高一點」,「身體再出去、出去!」,「腳踩下去!」這是一群台北國立藝術大學舞蹈系的學生。他們的身材修長、比例勻稱、技巧熟練,他們年輕而且美麗。但是全場你只能看到林懷民一個人的身體,你只能看見他一張臉孔。他一會兒呲牙裂嘴、一會兒咬緊牙關,他跳的比任何一個年輕的舞者都高、都有力氣,他的嘶吼聲也比任何人都來的狀闊,更充滿氣魄。他滿場飛舞,只為了激勵這群孩子們努力去體會「薪傳」的精神。不斷、不斷的練習,年輕的孩子們累了、乏了;他們跳不動了、想休息了。但是全場跑的最多、跳得最高、喊的最大聲的林懷民依然充滿了動能。
8月這群孩子就要遠赴德國,和香港;澳洲、美國等四所大學舞蹈科系的學生共同演出「薪傳」。這樣的因緣是來自一位澳洲的舞譜家─雷•庫克(Ray
Cook)。
Ray形容他第一次看見「薪傳」的時候,有好幾次都震撼到汗毛直豎。當下他便趨前向林懷民致意,並且表示願意免費為「薪傳做紀錄。最後花了四年的時間,「薪傳」終於被紀錄成完整的舞譜形式,並且永久生藏在紐約的舞譜局,以供後人參考學習。
西澳藝術大學舞蹈系主任南妮•哈莎(Nanette
Hassall)形容「薪傳有一種建築感,她說:「用許多身體建造出一種結構,在當代的舞做中已經越來越罕見;林懷民的作品非常神妙的一點,就是這種身體在空間中建構出來的圖像,非常吸引人。」
「薪傳」、「白蛇傳」、「廖添丁」、「寒食」、「星宿」,以及「家族合唱」中的「乩童」、「燒王船」等,這些來自傳統,來自我們耳熟能詳的神話、民間軼事,來自我們的土地、宗教、信仰…在林懷民的編寫下成就了一齣齣精采的舞蹈。
▲Top
.人間之舞 Dancing for the People
 1988年,「雲門」暫停。在苦撐了15年之後,負債累累的「雲門」終於沒有辦法再走下去了。暫停期間林懷民一次搭計程車,司機問他,「雲門」為什麼暫停?林懷民說了一些關於「雲門」經濟上的窘況和辛苦,司機先生非常的同情並且說:「我們每天開計程車,在台北市的交通裡面跑,也很辛苦。」最後林懷民要下車時,司機先生不肯收他的錢,他大喊著:「林先生,要加油!」 1988年,「雲門」暫停。在苦撐了15年之後,負債累累的「雲門」終於沒有辦法再走下去了。暫停期間林懷民一次搭計程車,司機問他,「雲門」為什麼暫停?林懷民說了一些關於「雲門」經濟上的窘況和辛苦,司機先生非常的同情並且說:「我們每天開計程車,在台北市的交通裡面跑,也很辛苦。」最後林懷民要下車時,司機先生不肯收他的錢,他大喊著:「林先生,要加油!」
「林先生,要加油!」是這樣的一句話,是這些點點滴滴的感動滋養著「雲門」、激勵著「雲門」為鄉親而舞,為歷史而舞。兩年後,林懷民宣佈:「雲門」復出!
從創團開始,「雲門」就經常性的巡迴至偏遠的鄉鎮,招待鄉親們觀賞;近幾年來,「雲門」的每一場戶外演出,觀眾都多達十萬、甚至二十萬人。作家陳映真先生說:「林懷民證明了,在鄉下的老百姓也有他們的美學高度,也能欣賞現代舞。」
於是我們看見一位西螺大橋旁邊賣西瓜的先生,因為節目單上寫著「不可穿拖鞋」,就趕緊去買了一雙嶄新的白布鞋。他說:「雲門」舞集藝術氣質不錯,下次還要再來捧場。」當我們看他拄著柺杖一跛一跛離去的背影時,忽然懂得了每次表演結束,雲門舞者與林懷民謝幕時的虔誠、慎重與莊嚴。我們更懂得了「我是男子漢」、「我的鄉愁」,「我的歌」、「明牌與換裝」,一個個血肉的身軀、血肉的生命。
擴大到對歷史,對全體人類命運的關懷,是「雲門」的「九歌」與「家族合唱」。香港知名的演員黃霑說:「讀屈原的『九歌讀了一輩子,沒讀懂。直到看見林懷民的舞作才懂了。』但對於不認識屈原,不瞭解台灣歷史的外國人來說,他們能懂嗎?美國亞洲社會節目部總監瑞秋•庫柏(Rachel
Cooper)說:「欣賞雲門的舞作是一種非常內在的經驗。在林懷民的作品中,不論是它的美感、他的簡約和他的豐富,你可以在不同的層次中進出、體會。」國際知名的舞台設計大師李名覺先生更強調:「沒有人有勇氣在一齣舞蹈結束時,不做任何動作,只在舞台上放八百盞燭火。而林懷民做到了!」
藝術家需要的是誠實與勇氣!我們看見在「家族合唱」理,舞者們捧著一盆盆水,洗去臉上的妝、油彩最後傾盆而下……;洗去了我們累世的傷痕和淚水,也滌淨了我們的心靈。
▲Top
.生命之旅
A Moveable Fea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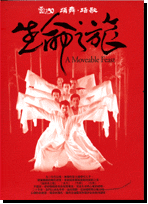 1991年,雲門在八里有了新家。這是一座按專業規格,用鐵皮屋搭建的排練室,從此以後舞者們可以遠離塵囂,在觀音山腳、淡水河旁練舞;而技術部門的工作人員,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實驗他們的燈光、佈景、道具。 1991年,雲門在八里有了新家。這是一座按專業規格,用鐵皮屋搭建的排練室,從此以後舞者們可以遠離塵囂,在觀音山腳、淡水河旁練舞;而技術部門的工作人員,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實驗他們的燈光、佈景、道具。
94年,林懷民已屆中年。當年那座燥烈急爆的火山,已成一座沉穩的大山。也就是在這一年「雲門」推出了「流浪者之歌」,林懷民說,他的作品變的很不一樣,是因為住到了淡水河邊。淡水河的安靜、漲潮時的波濤洶湧、太陽下的金光閃閃、風起時的變化萬千,以及時間的永恆都在「流浪者之歌」裡呈現出來了。誠如美國舞蹈節(American
Dance Festival)總裁查爾斯•哈瑞特(Charles L. Reinhart)所說的:「當你置身其中,時間彷彿不曾存在,所以似乎覺得這個作品有些短,而這正是它最輝煌之處。」
「流浪者之歌」講的是佛祖釋迦牟尼證道成佛的故事,在這之前林懷民已經多年走訪印度,靜心打坐也是「雲門」舞者每日必修的功課。靜坐之後「雲門」舞者開始學習太極導引,四年後林懷民編作了「水月」。英國倫敦泰晤士報資深舞評唐諾•胡特拉(Dnald
Hutera)形容,欣賞「水月」是一種「生命中深層的愉悅」。藝評家蔣勳先生更提起中年以後的林懷民,越來越希望能夠在作品中提供給觀眾一種生命提昇的快樂。而「水月」正好像是「把生命紓解到,像一 朵花在釋放、在開,這樣的狀態。」 朵花在釋放、在開,這樣的狀態。」
90年代「雲門」晉身國際一流的舞團,林懷民更是國際間少數幾位頂尖的編舞家之一。這一切的榮耀正是每一個「雲門」人與林懷民,一年365天,一天工作10小時,三十年不間斷換來的。
2000年雪梨奧運,「雲門」是全球被邀請的四個國際團體之一。2003年,國際間最重要的「下一波藝術節」(Next
Wave Festival)更三度邀請「雲門」至紐約布魯克林音樂學院(BAM)演出。「下一波」藝術總監喬•馬力諾(Joseph
V. Melillo)形容「雲門」的舞者為「純種馬」,他說:「這是我所能給的最高的讚美!他們在舞台上是那麼的美,因為他們的身體是那麼的美,這些舞者們擁有最高度的紀律與最完美的訓練,而舞蹈正是關於身體。」
2002年春天「雲門」在歐洲巡演,四月份來到捷克首都布拉格不幸的是演出期間,全團食物中毒。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上吐下瀉,連一向意志力最堅強的林懷民都病倒了。然而長期的訓練和培養,團員們展現了高度專業與敬業的精神,舞者們忍著副不的劇痛發著高燒,仍然堅持上台演出。謝幕時全場觀眾起立鼓掌,三
十分鐘不能停止。林懷民紅著眼眶走出來,到幕前單膝跪下,向舞者們鄭重致意。這就是「雲門」的訓練與紀律。
林懷民從最早在西方受了短期現代舞的訓練,到回國創立「雲門舞集」。舞者們的訓練,從芭蕾、現代、京劇、太極到武術,甚至書法。他們永遠對開發自己的身體有極大的興趣,林懷民也永遠勇於挑戰自我;年輕時的實驗之作「獨舞X3」,「夢土」、「九歌」中對他方遠地的嚮往,以及「焚松」、「夢竹」、「行草」嘗試開創更新的語彙,到2003年「?」的呈現,又是一種全新的風貌。
德國最重量級的舞評家約翰•舒密特(Jocheb
Schmidt)說:「林懷民是一位百分之百的編舞家,他結合了身體和靈魂、身體和思維。」,大陸知名的文化評論者余秋雨先生更強調,「以後世界各國的人要了解東方文明,要了解中華文明,最崇高、也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進「雲門」的劇場。」不過林懷民自己說:「編舞是一種工匠的行為,你只能不斷工作,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不要放棄任何可以工作的一點點時間和空間!」
30年,我們見證了「雲門」奮鬥和成長的歷史,我們欣賞了「雲門」最經典的舞作,隨著影作的鋪陳我們也和「雲門」一起悲喜交加。林懷民說,算命的告訴他62歲可以退休,而他也希望這件事情可以成真:如果一年編一支舞,我們大約還可以見到林懷民六、七支作品。雖然我們不知道林懷民或者「雲門」未來的美學會朝什麼樣的方向發展,但可以確定的是「雲門」會繼續走下去:努力而堅持的走下去。(編導:曹文傑)
▲T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