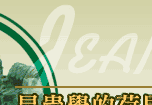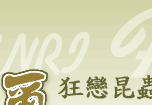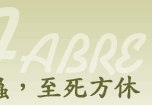|
法布爾遇上達爾文
雖然昆蟲記在科學、科普與文學上都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有關《昆蟲記》中對演化論的質疑是必須提出來說的,這也是目前的科學家們對法布爾的主要批評。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了《物種原始》一書,進化的概念逐漸在歐洲傳佈開來;廿年後,《昆蟲記》第一冊有關寄生蜂的部分出版,不久便被翻譯為英文版,達爾文在閱讀了《昆蟲記》之後深深佩服法布爾那樣巨細靡遺且求證再三的記錄,並援以支持演化論;相反地,雖然法布爾非常敬重達爾文,兩人並相互通信分享研究成果,但是在《昆蟲記》中,法布爾不只一次地公開質疑演化論,如果細讀《昆蟲記》,可以看出來法布爾對於天擇的觀念相當懷疑,但是卻沒有一口否決過,如同他對昆蟲行為觀察的一貫態度。我們無從得知法布爾是否真正仔細完整讀過達爾文的《物種原始》一書,但是《昆蟲記》裡面展現的質疑,絕非無的放矢。
十九世紀末甚至二十世紀初的演化論知識只能說有了個原則,連基礎的孟德爾遺傳都還是未能與演化論相結合,遑論其他許多的演化概念和機制,都只是從物競天擇去延伸解釋,甚至淪為說故事,這種信心高於事實的說法對法布爾來說當然算不上是嚴謹的科學理論;同一時代的科學家有許多接受了演化論,但是無法認同天擇是演化機制的說法,而法布爾在這點上並未區分二者。但是嚴格說來,法布爾並未質疑種化或是地球有長遠歷史這些概念,而是認為選汰無法造就他所見到的昆蟲本能,並且以明確的標題「給演化論戳一針」表示自己的懷疑。
而法布爾從自己研究得到的信念,有時也成為一種偏見,妨礙了實際的觀察與實驗的想法。昆蟲學家巴斯德(George
Pasteur)便曾在《Scientific American》(台灣譯為《科學人》雜誌,遠流發行)上為文,指出法布爾在觀察某種蟹蛛(Thomisus
onustus)在花上的捕食行為,以及昆蟲假死行為的實驗的錯誤。法布爾認為很多發生在昆蟲的典型行為就如同一個原型,但是他也觀察到這些行為在族群中是或多或少有所差異的,只是他把這些差異歸為「出差錯」,而未從進化的角度思考。
法布爾同時也受限於一個迷思,這樣的迷思即使到今天也還普遍存在於大眾,就是既然物競天擇,那為何還有這些變異?為什麼糞金龜中沒有通通變成身強體壯的個體,甚至反而大個兒是少數?現代演化生態學家主要是由"策略"的觀點去看這樣的問題,比較不同策略間的損益比,進一步去計算或模擬發生的可能性,看結果與預期是否相符。有興趣想多深入了解的讀者可以閱讀更多的相關資料書籍再自己做評價。
多元的啟蒙之路
昆蟲記》迄今已被翻譯成五十多種文字與數十種版本,並橫跨兩個世紀,繼續在世界各地擔負起對昆蟲行為學的啟蒙角色。希望能藉由遠流這套《法布爾昆蟲記全集》的出版,引發大家更多的想法,不管是對昆蟲、對人生、對社會、對科普、對文學,或是對鄉土的。曾經聽到過有小讀者對《昆蟲記》一書抱著高度的興趣,連下課十分鐘都把握閱讀,也聽過一些小讀者看了十分鐘就不想再讀了,想去打球。我想,都好,我們不期望每位讀者都成為法布爾,法布爾自己也承認這些需要天份。社會需要多元的價值與各式技藝的人。同樣是觀察入裡,如果有人能因此走上沈復的路,發揮想像沉醉於情趣,成為文字工作者,那和學習實事求是態度,浸淫理趣,立志成為科學家或科普作者的人,這個社會都應該給予相同的掌聲與鼓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與倫比的觀察家 ◎
磨難中的熱情
|